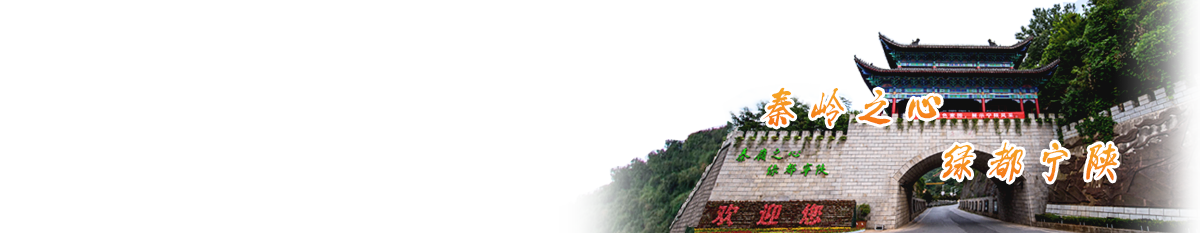打谷子
打谷子
家乡地处秦岭南麓,本地人喜食稻米,因此种稻谷、收稻谷是第一要务。祖辈们荆棘丛生、乱石成堆山脚缓坡上用钢钎撬、铁锤捣、乱石垒、畚箕挑,建起了层层梯田,再想方设法把山沟的泉水引来,造就了这难得“半分田”(家乡地貌称为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)。

我家的水田在屋后的塝田湾,只有一亩二分,水田的产出关系到一家人温饱。插秧以后,父亲一有空就往田边跑,内心的期盼和担忧如野草一样四处蔓延,直到看到纤细小巧的秧苗直立在绵软的淤泥里,由鹅黄转为碧绿,透露出生机,他的担忧才会烟消云散。伴着气温上升,秧苗一天一个样,整片梯田像是穿上一件淡淡的绿花衣,颜色也慢慢的由浅变深。
大暑时节,秧苗的团体逐渐壮大,挨挨挤挤,稻田已经找不到空隙了,它们正大口大口吮吸泉水,蓬勃着,孕育着。乡亲们的心,也随着成长的气息律动,心里一阵紧似一阵。白露过后,稻田在凉风中由绿染黄,乡亲们瞅着,眼睛里堆满了笑。
“下两河已经开始答谷子了”,出门的乡邻带回来秋收的信号像是一颗烟雾弹,消息迅速传遍村子的角角落落。家乡一直把收稻谷被称为“打谷子”,打字又转化为平声“答谷子”,我猜想可能包含着在田里忙碌了一年,庄稼对农人答谢的寓意吧!
中秋前后,稻子熟了。远远望去,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梯田,像一弯弯新月,像姑娘的百褶裙,一条条田坎像是美人的眉线,一切都美得简洁生动,如油画般的世界。父亲还是有空就去田边,习惯性的蹲在田坎上慢悠悠的点燃一支烟,淡淡的烟雾在他的头发上纠缠一会儿,然后飘散殆尽,最后望着天空,预测着今年的收成。有时他一边吸烟,一边手抚稻穗,一株株稻穗像是临产的孕妇,安详满足,我猜想那个时候他的一定内心充满了沉甸甸的踏实和喜悦。

村里开始打谷子了,那个年代,很少可以请的到临工,秋收都是乡邻帮忙,今天在你家,明天到他家,轮换着打谷子,掰包谷。父亲每天早出晚归,奔波在各家的稻田里,踏进家门总是带着一身疲惫和汗湿的衣衫。直到有一天,父亲乘着夜色开始收拾麻袋、竹席、借来拌桶等器具,我知道明天我家要收谷子了。第二天四下还是一片漆黑,空中传来断续而幽远的鸟鸣,父亲已经起身在院里嚯嚯的磨镰刀,母亲开始烧火做饭了。清晨,太阳还未破晓,天上浮着几朵轻飘飘的白云,到我家打谷子的乡邻陆陆续续到位,狼吞虎咽的吃了早饭,带着器具开始下田了。
打谷子的人分为两拨,一拨割谷子,一拨打谷子。割谷子伤腰,打谷子伤手(胳膊),最难的前三天“疲劳关”,忙碌一天,等到放工,累得走路都直不起腰,疼得手臂举不起筷子。天色微明稻叶上还沾着露珠,空气里弥漫着稻谷散发出来的清郁味道。割谷子的人率先发力,弯下腰被,左手揪住稻杆,右手握紧镰刀,嚓嚓的割谷声清脆利落,稻子一把把整齐的放在田中。稻田被迅速打开一个缺口,打谷人将小船一样的拌桶安放到田里,三面围好竹席,竹席上覆盖一张大油布,拌桶装扮得像一艘小帆船,最后放置一个木桥子,打谷人开始操作了。

打谷子一般两人一组,前面两人打谷子,后面两人握着稻穗等待,一退一进,进退自如,像是跳交谊舞;双手握紧一大把稻杆,抡圆了胳膊,稻穗在空中划出一个优美的弧线,重重的落在木桥子上,颗颗稻粒挣脱稻杆的束缚蹦蹦跳跳的聚集到一起。打谷子讲究两重三轻,开始两下重,稻穗要落得快,为了脱粒,后三下轻,是将稻粒从稻草上清理干净。有时候,一片梯田中几家打谷子,像是千帆竞发,百舸争流,加上嘭嘭的打谷声,似赛龙舟的擂鼓声,在山谷间回荡,此起彼伏,煞是热闹。脱粒的稻草往拌桶边靠着,集齐一大捆,农人熟练地抽出几根稻草,用力勒紧,稳稳当当立在田中央,像是一个个不倒翁,又像一片梅花桩。
打谷中途休息两次,人们开始插趣打诨,调侃邻家的帮工,某某人干活舍不得出力,主人家舍不得酒菜不如投靠到这边来,梯田里一时间充满了热闹的气氛。田里人头攒动,稻田在镰刀一点点的蚕食下,变得白一块,花一块,像是小丑的头皮。
新收的谷子带着水汽和清香,被装进麻袋扛回家。晒谷子的场地是门前的黄泥院坝,几家人合用,黄泥院子被石碾滚过,轧得瓷实干爽,像一面镜子,能照见彩云的影子。母亲用木耙把倒出来的谷子摊开,梳理成一行行整齐有序小山丘,像是梳理闺女的小辫儿,轻盈小心,最后搂去残存的稻草,场上的每一粒稻谷都是那样温润油亮,在秋阳中闪闪发亮。

夕阳西下,田里只剩下挨挨挤挤的稻茬像箭簇一样直指天空,透露着一丝悲壮,像是和季节道别,布满了伤感和离别。乡邻们收工回家,享有一顿丰盛的农家菜,腊肉是必须有的,养了半年的大公鸡也被端上餐桌,在推杯换盏之后,大家带着醉意离去,准备第二天的忙绿。
八十年代,水稻大都施农家绿肥,火肥(焚烧的草木灰),稻米香甜软糯。新谷剥壳出了第一茬新米,母亲首先要喂饱我们,她将新米煮得六七分熟,再捞出,锅底放一层炒得金黄的洋芋块,覆盖半熟的新米,细细柴火蒸的满屋飘香,米饭中渗透洋芋的香甜,锅巴清脆,让我们饭量大增,回味无穷。有一年外出到陕北学习三个月,每天小米馒头,第一思念的是亲人,第二想的就是家乡的洋芋米饭。
去年中秋回家,母亲做了村里的新米铁锅饭,可总是吃不出当年的香甜和味道。父亲若有所思的说,如今梯田大都变成了旱田,剩下的稻田争高产施化肥,有人种田,无心管理,哪还长得那时的味儿来…
- 上一篇:秋雨中在宁陕看到的秦岭,美成了这个样子…[ 10-15 ]
- 下一篇:美丽的家乡·陕西宁陕[ 11-18 ]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