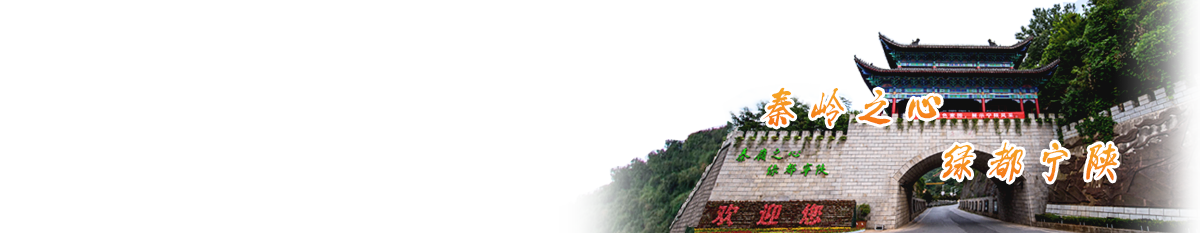春天的怀念
春雨如期而至,站在老屋的窗前,望见菜园里的小路边已经开始泛绿了。以前每年这个时候,身材瘦小的三伯母都会在菜园里忙碌着翻地、起垄。去年冬天,她永远的走了,总觉得菜地里少了什么,心里多了一份怀念和愧怍。
去年几个亲人、邻居相继去世了。这些年,故土上每天都在发生变化,有生死离别的大事,也有鸡毛蒜皮的琐碎。从父母口中得知一串串熟悉又陌生的名字,他们或热情或冷漠,或勤劳或懒散,他们和村里的各类悲喜剧,家长里短,让人的情感跟随故事起伏跌宕,悲喜交加。
三伯母性情极为温和,心地善良。幼时记忆里,瘦弱的她每天总是扬着喜盈盈的笑脸,一边推动石磨,一退一进,一圈又一圈,还不忘照顾堂哥和院子里的几个小孩,一块火烧馍,几片饼干,我们可以围在她的身旁快活的玩一个下午。在悄悄地岁月里,我们兄弟三人也受到了无私的照料和馈赠。
祸不单行,受尽病痛折磨的二伯也在万家团聚的中秋节,半睁着眼睛悄无声息的走了,大眼睛像当晚的月亮一样惨白。
作家余华说过,父母健在,我们和死亡隔着一条垫子,父母不在了,我们就直接坐在死亡之上。
这些年随着年龄增长,参加的婚礼和葬礼的次数大致相等了,都有感人的泪水,都很热闹,都有离别,只是归途不同罢了。
在香薰火燎中,我围着朱红的棺木,转了一圈又一圈,像是拉磨的毛驴,完成一项任务,完成一种仪式,耳旁叮叮咣咣的锣鼓声,让本来嘈杂的环境,蒙上深沉的忧伤,像是层层涟漪在亲人的心头脑海中荡漾、推进,裹挟着痛哭声消失在夜空里,直到无影无踪。
在乡亲们的簇拥下,我们把棺木小心翼翼放入墓穴,就像埋下一粒种子,希望他入土为安。天空灰暗,飘落细雨,匠人们把石块一点点垒砌起来,最终变成了一座矮矮的坟茔,一长串鞭炮声后,众人怏怏离去。
故土就是这样一片土地,有父辈流淌的汗水浸渍,有母亲回荡在田野里一声声急切呼唤,还有村头亘古不变的老梯田,那些都是与生俱来的熟悉。那些匆匆而来,又悄悄消逝,不光是岁月和容貌,更是难以言说隐痛和自然生存法则。
印象里,二伯是一位勤劳固执的老人,沉默寡言,直言直语,极少的言语中夹杂着呛人的味道。但他的心底却是善良,见到蛇虫之类,都会驱赶放生。有啥好吃的,也从不吝啬的招待邻居旁人,从不记恨被人的过错。几乎每一个清晨,他起得很早,扛着锄头下地了,指直到日上三竿,才带着一身草露步履沉重的归来。大都黄昏的路边,他用沟壑纵横的大手夹着纸烟,憨憨的一笑,露出粗糙发黑的黄牙。
村里每年都有人悄无声息的消逝,像是村子上空刮过的一阵风,来过,喧嚣过,热闹过,最后随风而逝,却未留下一丝踪影,只有亲人残存的记忆。他们诚实、固执、勤劳、善良,大都无暇顾及外面世界的灯红酒绿,在大山的褶皱里扎下了根,从生到死都未离开过故土。他们历经无数的阴晴雨雪,终其一生都围着灶台、菜园,将所有汗水洒遍梯田、坡地里的每一寸土地,滋润过每一粒粮食,付诸毕生期望和心血,无论丰收还是欠收,都对土地充满热情。一旦闲余,他们将土地里长出的最大最漂亮的蔬菜,背到城里,经历漫长的等待和不厌其烦的讨价还价,换来一叠花花绿绿的小额钞票,心满意足的归来。他们的一生也数不出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。
时间是一条不可逆转的河流,不断地向前流着,不动声色的改变着一些事情,比如一轮月的圆亏,一朵花的荣凋,一个人的衰老、消亡…
草还会再绿,但人不会再来,光年犹走,追忆绵长,也许我可以从记忆长河里打捞那些失落的乡愁和美好…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