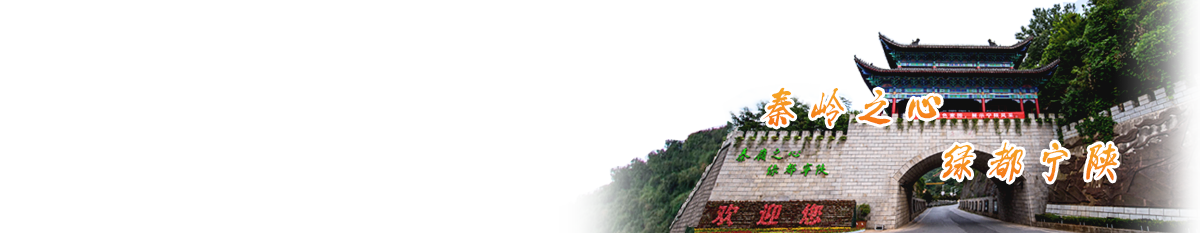淋点雨(散文)
小时候读过一首古诗,说是一个披蓑衣戴斗笠的老汉,独自在寒江上钓雪,印象极是深刻。以后,在老家寄住过三年,每每看到祖父在下雨的日子,也同样地头戴了斗笠、身披了蓑衣,去到村头山边前的庄稼地里,看庄稼,在雨中给庄稼地抽水沟。有时雨下得久了,便去把田缺子拔了,快要翻埂的田水渐渐地就消下去了许多,正怀着胞的水稻,身子也就正稳了,任雨如线如柱地敲打着,直是生机得盎然了。玉米地里,黄黑的泥巴膨胀得快,像是有了地力向外直拱,雨打着包谷叶子、杆子,撕扯老布般地响,地里很快就叫雨水拱得水沟纵横,一片水的油光。祖父就在地头抽出更大的沟来,叫雨水挨着地边、从庄稼的门前改走了闲路,免得包谷杆站立不稳,伤动了根茎了。
站在老宅子的阶沿前,远远地,是可以看见祖父雨中的身影的,像极了是一只黑黑的大鸟,正在雨中护着巢哩!山里的雨下得水雾腾腾,原本眉目清楚的四围的山,刹时便只落得一道灰黑的轮廓了。两袋烟的功夫,祖父从雨地回来了,浓密的雨幕中,祖父像是不断地拨开雨的帘子,也像是一个歌唱家从大幕里出来,要当着千百人的面唱起一曲大歌哩。祖父停在偏厦屋那边的谷仓房前,在墙边上掎靠了手中的家什,再慢慢腾腾地摘斗笠、解蓑衣,他的腿脚、胸襟已然湿透了,竟往下直滴着水珠子,摘下的斗笠、蓑衣挂在山墙头的竹钉子上,也是一道粗粗的水线往下直淌,一时便把山墙沥得一片水印。然后,祖父伸直腰板,望着雨幕,双手在胸前搓动,发出耒子磨谷子般的声响来,好一阵儿,直长出一口粗气来,脸上有了些笑意了。
多少年后,我渐渐地理解了,祖父雨中归来后的笑意,是面对着庄稼旺势的笑意,是谢承着一场好雨的笑意,那时节,庄稼需要雨水,节令需要雨水,估摸着秋后一定有个好收成的祖父需要雨水,已然干巴了许久的祖父的蓑衣、斗笠需要雨水,那些先前就快要有了锈迹的农具需要雨水把自己磨亮,在雨水中,乡下经历着生长的一切物事像雨中的叶子那样发亮,发软,叫人心里感动着天地的实诚,在最需要雨水的时节,雨一点也不做作地下过了。及时的雨,是乡下人的娘老子,娘老子在,家院里才长有烟火气,才有菜香饭香酒肉香。小时候在老家,正是三伏天里,我是经见过一连两个大月不落一丝雨的。地起灰了,山涧里水露出半乍厚的青苔,那些春热后原本生机着像半桩儿娃的包谷叶子卷了筒了,似是一把火都能点得着,水稻像乡下经血不调的女儿,直是怀不上胎了:生产队里发一声喊,男女老少一二百人,一齐地担了各式盛水的家什,从老山涧里担了水救苗子,从早到晚,通天白夜地不歇工,真是百里千担一亩苗,硬是把三四百亩庄稼浇了一遍!说来也气,刚浇完地,天便下起了瓢泼大雨,这雨下得妖气十足,直叫半村人大哭不已,即是欢喜,也是悲愁了。
我是喜欢时常地淋点雨的。秦岭的老林子里,是雨的家乡,动辄就给你蒙头盖脑地下起一场你不曾预料的雨来。林子太深透了,积聚了不知多少年的水气,有水便有气,有气便会生成了雨。除了冬季,春夏秋,常常就是雨活动的频繁季。在山里走着,正在高兴天气的大好大晴哩,不时脸面上就有风扫过,路边的树棵子里、草丛里,便冒出一些水的气息来,敏感的人,一时就知道了:天要落雨了。悄没声息的雨,一如乡下场院边打盹的老猫,看着是懒倦得毫无斗志的,也像个退二线又看透官场的老干部,任什么也激不起兴趣,突然地那老猫便警觉起来,半弓起了身子,脚步也站立起来,头脸朝向了一个方向,眼睛直是瞪得亮圆,一时箭一般地窜起,射向场院边的草棵子里了,那草棵里立时也响起一阵叽叽的、哭哭的撕咬声,片刻又静了:一只大胆的老鼠被老的猫捉住了。如此的雨便是这样来的,没有事先的声浪,一时就下了,骇人一跳,很快又停住了,把人的头发、眉毛弄湿一下,把肩头或胸前的衣服也弄成了半湿了。这样的雨,好比乡下讲究人家的尘掸子,主人或客人进得家门,讲究的女主人必要用了尘掸子绕前转后地拍打几回来者身上的尘土,一时就亲近了,有了回家的感觉了。这样的雨,我喜欢叫做洗尘雨,属女性,手脚轻柔,颇多温情。乡下春秋两季,如此的细雨便多见,地面正当起了尘土了,雨便下来轻轻盖一盖,天地立时清爽了许多,叫人心情大好一番。
大的雨往往是有前兆的。如是天边起了云层了,渐渐地从山谷间、林梢上,或河水面上,升起一派雾来,水气渐渐地浓透了,此时没有风,或感着有风,那风只是闷着不大刮,空气中有尘土强烈的灰腥味了,你正犹豫着是紧跑几步就近找个人家或岩洞躲了这雨罢,雨脚却早下将到地面来,溅得地面的灰土腾起烟来,只听得“哗”地一片大响,一天的雨便倒倾下来,立时天地间直是塞满了水线与雾气,在雨中还未跑出几步的人儿,已经成了水中的大鸟了!如是闲走罢,也便欢快地激起一片大喊大叫的夸张的人声,男人的嗓子如狼,吼吼地有力;有时女人相跟着,本是闷了一路插不上话哩,此时便发作得痛快,尖起个声音,叫得有音乐感,也趁机直往信得过的男人身后躲闪,却哪里躲得过雨去!一时男人女人都湿透了。男人们湿了,身个儿往往并不好看,像一些怪怪的山子石或老枯的木头。女人却洒脱些,一些平时衣服盖着的曲线便都叫雨勾画出来,雨中便有了大大的韵致了。这是夏日里的雨:痛快淋漓,一时叫人做了一回无拘无束的人哩!只是夏日里的雨倒是寒气沉重的,雨把心头的热逼退了回去,此时需要快快地找了人家,熬上一锅姜汤,辛辣地喝上一气,一身的冷逼成满头的细毛毛汗了,好比脱胎换骨了一般。大雨过后的山影清碧,如同绘画,河水泛起浪花,树草纤尘不染,如是雨后阳光重又大作起来,常常必是有彩虹的,从一座山头跨到另一座山头去,三种颜色在幻觉中变化得无穷无尽,风似乎在敲打着那虹,声响得空阔清越。
因了喜欢雨,我便是一个最不记得带伞的人。有时出门,别人半善意地提了醒了,便也正经地带着,转身开个会,访问个人家,或在路边停了一停,那伞便不知了去向了。我是伞很多,一时没了便去买上一把,或别人送来一把,手边却少有用得上的伞。想必我本不是个爱伞的,那伞也多半对我失望得很,瞅个空子,自己溜走了。身边有些朋友,工作生活极是讲究,比如这出门,必是要看了天气预报,大凡有些预感了,便是要极认真地带了伞的。如是正好遇见雨了,朋友便从容得很,而如我从不喜带伞的,一时有些尴尬起来。有时也敬佩朋友来,想人家活得多么细法,是我所不如的哩!只是临了雨,我还是喜欢淋上一淋的,别人给我备了伞了,多半也不大用,提将在手,似是故意把自己淋得半湿,打几个激灵,骨头缝似也进了雨水了。朋友每每说我粗心得很,我也有时惭愧一二,过后,还是忘了带伞了,天性如此,别人一时是教不转的。
乡下勤快的老人家,常年在地里刨抓,喜欢遇雨时披个棕蓑衣、戴个竹斗笠,而不是打个伞呀,披上件帆皮布的雨衣呀。早年在乡下时,我也曾试穿过祖父的这套行头,直是适合在雨中干活穿用!棕蓑衣看似厚重,其实蛮轻透,再大的雨水,早已从棕面上滚落走了,竹的斗笠也不甚积水,把直落的雨分得四散走了。这样的装扮,在雨中重活轻活都可以自如地干得,也透气,清爽中有暖意。如是想到那古诗中钓雪的老汉,一副农家的装戴,阻隔了天地的寒意,心中直是独独地运发着自己如诗如画的心机,真是有了大趣的。说到雪,那是雨的另一个生成罢,只是没有雨的多变,一律来得散慢。山野里的雪,尤其是做足了起势的。天渐渐地阴沉了下来,雪花似有似无地飘洒在半空,渐渐地大将起来,如是深冬的雪,便下得一步紧似一步,从细毛毛雪,一时幻化得满天的粉蛱蝶了,更猛些时,便是大朵的棉花。杂色的山河,很快通体雪白,纯净得极不真实了。光头光脸地在雪地里走动,是经雨般的另一大趣,需要静心静气地不理睬那雪,任它落在身上、毛发上、脸颊上,不要用热的呼吸去激发了它,直到毛发上凝出冰凌来,心倒是越发地静了。静中毛发上的冰凌相擦着发出只有自己一个人听得分明的清音,细碎而通天。我曾在秦岭的大雪飘飞中走过三个小时的山路,开始还和同伴说着话,斗个嘴,很快都无了声息,雪在脚下加厚,山林无语,雪中人无语,因了雪的洒落,天地都是无语,无语中的我,极是想见自己其实就是一棵行走着的树木了,在雨中在雪中生机不减,摇曳或静谧。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