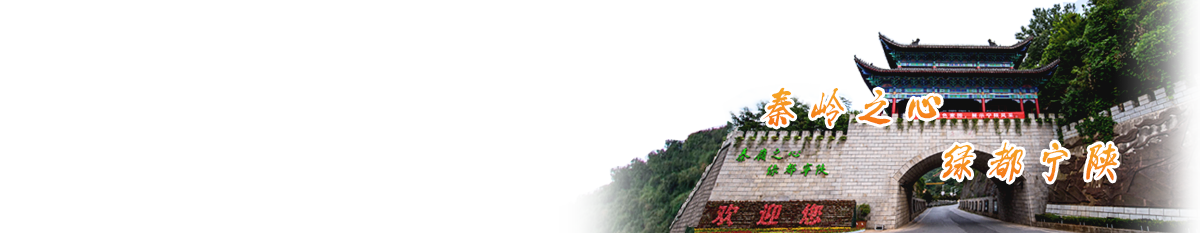清水养鱼
对鱼的记忆甚或早于其它肉类,是我至今都疑惑的事。早年的老家,深沟大涧的,浓阴的树林和浮而不散的水气,常常叫林子中生出过多的阴森。如是八月大暑之际,走在阳坡上,或爬坡,或下坡,或走毛毛细细的砭子路,总是有一身大汗要出的。微风不解暑气。即或一阵长风吹来,也是热浪的感受,真是不吹来也罢。唯有走进了深深的林子,一如走进了低冷的空调的屋子,原本全部张开着的毛孔,竟然一刹那的时间,统统地闭合着了。巨大的不竭的林子中的冷气鼓面而来,渐渐地如同跌入了冰窖。夏日在林中不可久坐。天上的暑气,地下的冷气,这样在你身心里相交着,如没一副担山的身板,差不多极容易就将一个好好的人激垮架了!有经验的山里人进了林子歇息,只片刻就要吆喝着起身的。说林子阴气重,坐久了,从脚根就进了脑门了,眯眼歇着,浑身便渐渐软得无骨了,想起来时,已是一堆泥了。
林子中的阴冷之气,自然源于林子中的水气了。大林子中必有大水的气象。林子的根须之下,是水的丰茂世界,它叫林子招摇而疯长。那些水,一部分是化作了树杆树枝树叶的,也或春天的繁花,也或秋天的果子。一部分化作了林中的水气,叫树林水色十足,也化作了林间的湿冷的,氧气太盛大了,进了林子,人与植物多半都是要晕头转向的。这还不算。老道的上好的林子,人不去破坏它,几百数十年间,望着林子的,傍着林子的,以林子为衣食的,进了林子的,出得林子的,只是力量太弱小,林子年年依旧,人只是它林中一只蓬间雀,叽叽喳喳了一辈子,还是蜗在林子的毛棵丛子里,或者只是在林子的边缘扭结了一生,也像是一粒极碎小的草籽而已。大气的林子,从未向人真正敞开过。比如我要说到林涧中的深水。有一个词,叫作“静水深流”,很是有想象力和扩张力。这词,正经只有在大老林子中才可体会得。水深而静,是有道理的。也唯其静,其流则深。我每每想见这词,无一不油然忆起大老林子的深透而明澈。忆起林中的深涧,那阵阵鼓腾而来的水气,那隔着层层林子都可明确地袭入耳鼓的水声,沉重而有磁性,是被树林过滤了的,是去掉了杂质的,繁复而条理清晰。穿过重重林木,或断崖,或缓坡,或水淖,或草甸,寻着水声而去,到底会看到一条林中的河流,在林中反复折射的光线中,闪着水花花的光斑,在杂草丛生的河岸,或大水冲激过后的裸滩上,各类叫不出名目的落叶、杂花、水蔓、彩石,以及各类小小的在水面划出细细波浪的水生物,叫你第一时间手足无措。如是静水,必是在林棵间款款而行,像极了一位山中隐修多年散步的古者,对外物一律地视而不见,水中映出来访者的面容,但那古者般的水的心目中并没有你。如是跌水,必是经过了一段乱石的,或是一堵断崖的,或是一段有着坡度的河床了,水像煮得盛开,碧绿的水色一律地变成雪白如玉的水花来,随着不同的段落,发出不同的声音,或如细琴,或如暗鼓,在乱石间的水浪,有吞吐之音,想那乱石下是有着巨大身躯的水怪的。在崖上跌下的落水,声浪骇人,音波刺人耳鼓,跌水砸击潭面激发起一圈圈腾起着的水雾,向四周扩散,如始不竭。如果运气好,在晴好的午后,没准也能看到水雾中荡漾而起的彩虹,如同神幻。这虹,往往更参差地勾勒出大老林子的丰硕,你不明它的终究,走不出它的深透。
就在大老林子中的河流中,生长着典籍中绝对找不出的各色土鱼。如林子中那些古怪的兽类一般,鱼是林中之河的精灵。每一种水的姿态,都对应着一种古怪的鱼。在跌水后面,那些阴岩或隐秘的洞穴中,生长着与森林同样古老的鱼,身躯黑丑,有四肢,头额扁大,啼声如婴儿,山里人称作娃娃鱼,拟声拟形,都是准确的。娃娃鱼颇懒惰,只在阳光照射良好时才出外进餐,也不寻觅,卧在浅水中,半张着大口,等那细小的鱼虾自动入口,入得口时,才猛然合拢,虎咽而下了。早年山涧里的娃娃鱼极多,入夜常听见一片嘈杂的小儿哭,山里人以为神性,多少年便从不侵它。大吃娃娃鱼,只是近年的事,渐渐地深涧中不见了它的身影。起先是山外人进山来捕捉,几乎用一简陋的编筐即可从容获得,入城即可卖出天价。于是引得山里人也自去捉拿了,转手卖给城里来的贩子。时间久了,浅林地段的娃娃鱼少了。哪里还有得,在哪道涧里,需走得多少弯折的山道,只有山里人知晓。城里山里成了同盟,一个捉一个贩,合作得甚是愉快。只是鱼是越捉越少的,没了娃娃的哭啼之音,大老林子间,却是少了神气了。翻花的河段,也是有鱼的,那鱼极是精明,有两种最为有名,城里指定着收购:一种雪白的翅膀,一种鲜红的翅膀,名字简单,便叫白翅膀、红翅膀。最长只能长到半尺,约摸半斤重,因是冷水中生得长久,又是与水浪捕击着的,那肉质便十分地活泛,且鱼刺如梗,易于理抹,做汤干烧,都是绝品。这两种鱼,以翅膀出名,翅大而色亮,便灵动得很,一闪身就不见踪影了,极不易捉拿,如是漫水里瞎捉,多半是无功的。人便想出一个办法:在半河里用石头柴草围了河堰,河堰的下出口,做了漏斗,人在远远的上方用木棍拍水,直赶得鱼们齐齐地向下游逃命,一时都跌入漏斗了,鱼的精明便很容易叫人破了。静水中出一种细毛毛的山虾,成群地在小小的水湾子里群栖,用了网兜就可捞得。毛虾做清淡的汤,也是上品。在细沙积得的漫滩间,生长一种钻沙的鱼,山里叫沙棒子。名符其实,圆滚滚的样子,甚是馋口。此鱼甚蠢,随便一种方式都好捉。有时见着了,用一根树条猛地抽打下去,水花溅处就晕了,立手可得。沙棒子一身的肉,似乎连刺都是没有的。山里有一种吃法,是用了沙棒子烩豆腐,汤白而鲜活,坐月子的女人可发奶水。近年也上了城里的餐桌,价钱不菲。在乱石间的,有一种鱼,形似娃娃鱼,却不是,身躯小了许多,它能两栖,天热了,栖于石间,专吃乱石间的绵虫,天若降了温了,它会一早一晚爬上岸,在山石上晒太阳,以积蓄体温。这种鱼也可口。只是要干吃才好。比如夏日里捕得了,一般是要晒干的,到了秋里,烩酸辣汤吃,甚是解酒。除了这两栖的鱼,山螃蟹也是有名的,它也是活动在乱石间的,铜钱大小,去了肚腔,用灰面裹了油炸吃,如嚼脆骨。
老林子间的野气,养殖得口嚼的极品,我的记住肉类,的确是自林子间的鱼类始。小时候在老家寄居着,猪肉吃得,羊肉吃得,老母鸡吃得,半造子的童子鸡爆炒青辣子吃得,只是单单记住了鱼。尤其是白翅膀,红翅膀,以及沙棒子。入秋后,天气渐渐凉下来后,我的大伯父或我的小老表们,便会进到林子里整鱼。那时候鱼多,秋天很快就浓透了,干鲜的鱼捕得回来,做着各样的吃法,顿顿不厌。比如有时沙棒子是丰收着了,竟然与面疙瘩一起烩了吃,这是一种极其败相的吃法,很是暴殄天物。以后在城里的餐桌上,见着山里的沙棒子,一盘子上桌,问价钱,竟然百多元的,一时伸出的舌头收不回去了!林子里的清水,养殖了水中的好鱼,进入记忆,便没法湮灭,在无口腹之趣时,有时想起往日的吃相,每每叹息连连,以为今不如昔了。在自然界的鱼整完之后,人们开始围塘养殖。我只是从不吃鱼塘的鱼。死水中的鱼,粘了太多的死泥的腥气,吃鱼如吃死泥。每每看到农人掘了水田,挖出方圆数十亩的大塘来,将水引入,投了鱼苗,一时养将得鱼大如小儿,运到城里去,竟如猪肉般砍切着卖,让人看着直是一无食趣。一些地方用沼渣喂鱼,或干脆用了粪肥之水喂鱼,那鱼便长得更其神速,城里人不晓得它们的来历,还是吃得口滑,就了酒大呼小叫着快活,我只是从不吃它们,无鱼也罢,宁可食青菜了。老家人早些年整山鱼时,很是赚了一些好处,便时刻念记着鱼是可以发财的。林子里的鱼少见之后,他们便自养,家家在房前屋后挖掘了大大小小的塘子,先是养殖白翅膀、红翅膀,不成功,又养沙棒子,依然不成功,最后改养大路的草鱼,好养,用了麸皮、豆蔓子草就可养活,冬季里捞起来,远远地挑到城里市场上批发,或零卖,每每就亏了本钱了。挑了最有长相的给我送一些到家,我却转身送了人了。山里的亲戚们不知道,还是年年送,也害得我年年转送人。有时也问,大老林子里的清水中的鱼,真的没有了吗?!老家人说:老实没有了,也怪,说没就没了,连鱼种子都难找下了。
秦岭山中这些年时兴起养殖冷水鱼,一时名气大作。冷水出在高寒的山里,一般在海拔1200米往上,沿了山沟沿边,修起水泥的池子,从上水头修得弯曲反复的堰渠,将山涧里的清水引到池子里,便养殖起山里的鱼来。那池子是有下水口的,那水便也日夜流动着,池子里永是一池不腐的清水。清水中的鱼,正经的叫虹鳟鱼、金鳟鱼,属于北方俄罗斯的鱼种,近些年在山水未损的高寒山里多有引种植养殖。此外也有俄罗斯鲟鱼。鲟鱼没有鳟鱼好养。鳟鱼凶相,吃法残烈,竞争中长得快意。因是长流的清水,水温一般在12度左右,很适合胃口的蠕动,大群的鳟鱼在水中不知疲倦地游动着,集体寻找着食物,看花了眼,很像是一阵阵的狂风,红的风,黄的风刮过来,又刮过去,清水中映着蓝天白云,那红黄的风又疑惑是在天空中刮动一般。每每喂养者投了鱼食进去,立时地池子里一片激越的水响,像是困难年月蜂拥着吃大食堂,又像是春运时节的抢火车,眨眼间,食物便消逝得干干净净。有游人投了面包渣进去,轰地一声就形成一股水浪,投入一根青草,也是抢得强弱毕现。鳟鱼从苗子进水,一年间就成长了成体,两三斤重的正好食用。清炖、红烧、吃生鱼片,都好。只一宗,要鲜活时吃,死后一小时,便有了毒了,这倒如河豚一般了,鲜美而有毒素,大生吃相时是要伴着若干的小心的。因此,秦岭山中的鳟鱼多半是城里人进山,在农人的池子边上吃的,眼看着从池子里捞起,也眼看着上了砧板、下了油锅,这才放心地吃。山里的池子越发地建得多了,城里人也越发地来的多了,来了,凡有鳟鱼的山沟里,必是要吃一吃清水中的鱼的。有时看着城里人吃清水鱼的样子,便想笑,终于没有笑出声来,想我们人其实是越发地可怜着了,连口鲜鲜的鱼汤,要得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