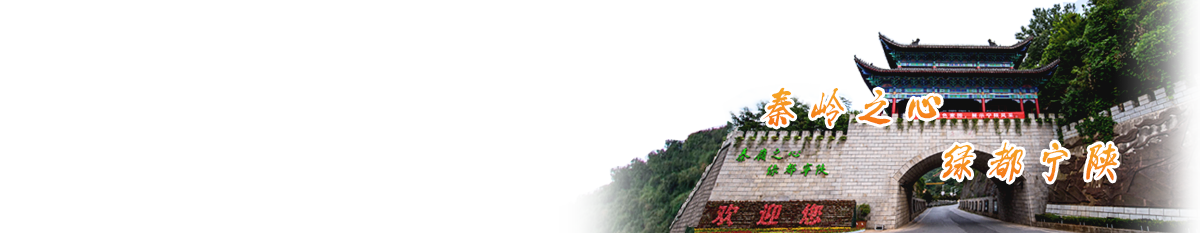雪玲珑
雪下得好了,我小姑夫就拿雪来洗澡。
在早年的四季记忆中,春天刮风,夏天走蛟,秋日起雾,冬天便得下雪了。哪一年竟没了雪下,没有了雨下,没了雾罩了,没了小刀子一般的风吹了,那一年便是要有了灾了。乡下人迷信,说道:这一年老天必是要罚人了罢!四季有象,一打开始,就给人间放着信息了,今年早知晓,从冬里就知道了,从春里就知道了,从夏里就知道了,从秋里就知道了。
春天不起风,庄稼尻子松。夏天不下雨,田里收糠秕。秋雾不浓,果菜发红。冬天雪脚浅,不怪穷人懒。下雪,在早年并不奇怪,到了冬了,有一日天阴着了,小北方沉沉地刮着了,有知识的人就说,天是要下雪了:果然,夜里或午后,那雪就下了。一般地,第一场雪是试探着人间哩,往往下了薄菲菲的一层,一指头厚,直简单地把路呀、街呀、墙头呀、树梢子呀、园子里的赖白菜、水萝卜呀,简单地遮一遮,权且便叫个雪了;第一场雪,是试着天底下的人家过日子,是沉实的哩,还是囫囵个儿的,第一场雪是叫人备着过冬呀,冬田翻了没?园子里的赖白菜扎了稻草没?过冬的柴火备够了没?城里人,坛子里过冬、过五黄六月的腌菜备齐崭了没?院子里、门前的阶沿上或后檐沟的场坝里,新备下预备要烧了一年的石炭了吗?第一场雪,是给懒性的人家一个信息了,再下一场雪,就要封了冬天的大门了!
小时候,常常记得天地间的雪下得都是大势的。雪大,雪厚,完全不同于普通的雪的,不同于如今苦苦等来的雪的。在早只记得从秋里开始,雾便常常浓重得烦心,常常要遮了日光,半天亮不起来。雾过后,世上的一切,都得是水浃浃的,手摸过的,脸蹭过的,鼻子呼吸过的,屁股坐过的,都是潮乎乎的,潮而阴冷,这便是深秋了,积攒了渐渐走近的冬里下雪的气势了。下雪那天,不到向晚,太阳起先还在偏西的云层,通亮地泛着白光,小城里的大小房屋,向东边随性地斜拖着粗大的光影,还有城东头的、城西头的大皂角树,桂花树,也是拖着粗大的光影,风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,并不冷峻,直是每一阵风起,便有些力道,像是力大的人扳腕子,一下沉,忍一下,再沉一下,便把对手扳倒了。慢性的风中,透着大势,果然是大雪的前兆哩:遇到的大人都说,要下雪了,快快地回家去呀!
下大雪的天气,我们一定要去玩雪呀。如果雪下得小气,我们便蹴在屋子里抱火炉子。看地炉子的炭火,或红或蓝地发着光,看火头上坐着的铝壶,吱吱地响着水声。家里的几个电壶早灌得满了,便任铝壶自个儿瞎嘟嘟。水汽把屋子激得潮烘烘的,下晚电灯的光在水汽中便显得发红。早间有盐没醋地吃了一顿烩饭了,或一顿包谷糊糊就酸菜了,雪天无事,就一定要坐在火炉边,渐渐地憧起瞌睡来。下晚间,吃过一顿萝卜干饭了,饱与不饱,也渐渐在火炉边憧瞌睡。那年间,直要下了雨了,下了雪了,出不得门了,饭后,瞌睡就要上到鼻子尖头,脑壳一冲一冲地就睡着了。坐着椅子就睡着了,歪在床上就睡着了,蹴在门槛上,也能睡着了。睡着睡着,大人一声吆喝,一个激灵便醒了;大人不吆喝,要是庄子里狗儿咬声一片价地像下雨哩,也竟不会醒!自睡自的。我上小学以前,整天眯糊糊地,到校里去上课,坐在课桌子后头,只要老师一讲话,课本翻得一响动,瞌睡虫就爬出来了,必定要大睡一气的。老师刚一叫醒,木木地望老师一笑,头儿一歪,又撞到课桌上,睡着了。害得老师上我家里去家访,给我母亲建议说,你们娃儿莫不是有啥毛病,要去医院里看一看哩。我母亲说,啥病?懒病!现在看来,那时的我,确是没甚病的,就是眯糊,且变天时便要眯糊,如下雪呀,下雨呀,天阴着了呀,都要眯糊。天晴着呢?似乎没甚记忆了,天晴心情一般大好,想必不会眯糊罢。
下雪天,大中午的,也眯糊过了,或者正想眯糊了,有小人儿来,在我们家大门外头,大声寡气地叫我名字了,我们也牺牲了眯糊,去雪地里疯张的。六七岁以后了,下雪玩雪,我们便玩得苕兴,打雪仗,渐渐往死里打,把雪疙瘩团得石块子一般,一个个追着往头上揲,打不坏人,打得可生疼,往往雪团子在头上炸开,雪沫子溅进衣领了,就也溅起一阵嘲骂声,雪沫子冰人,棉袄里半天清不干净,早已化成水了。小气些的,索性大哭起来,说,你妈的个瘟,把老子衬衣都搞湿塌了!硬气的,非要追了上去,必得报了一球之仇,有时把敌人摁倒在雪地里,直接抓起雪团子,往脖领里塞,这仗就打得有了气象,热火,几天下来,小人堆里还要谈论得热烈,比谁个利害,手准。如果有大雪,我们就在河岸上雪厚实的地方,垒雪窝子,雪窝子能钻进三四个人去,有时,我们也捡了些野柴,在雪窝子烧了一垄火了,围着火,说些天上地下的事:那时,我刚看了《林海雪原》,我给大家讲少剑波、杨子荣的故事,讲英雄们在雪窝里生着火了,用树枝子当叉子,在火头上烤冻粘豆包子吃。我们都弄不明白粘豆包子是个甚物儿,想象一大气,都说不清楚,有说小豆包子的,有说腌菜包子的,有说四季豆包子的,反正都是包子,便激起我们的一派向往:下雪天,有包子吃,多么的幸福呀。我常常就感叹,说:这就是社会主义呀!白茹,自然是讲得最多的,书上的情节讲完了,我不觉中就生发些情愫来,随性地编排一番,讲得手一摸就够着了,肉肉的;一抽鼻子,就闻着了,香香的;一睁眼,便看着了,秀秀的;我说,你们晓得不?白茹呀,像我们一个老师哩!大家就猜,一齐猜,有猜着了的,有猜不着的,我都说不对:只有我一个人晓得,是谁,她白的皮肤,小的个子,说话嗲声嗲气地,小小细细的,她身上一到冬天,就要散发出一股雪花膏味,这味道,害得我至今都以为最好的护肤品直是雪花膏的。她就站在我们的雪窝子外头,在太阳光下一晃一晃地耀眼。有不老实的小子,叫我的白茹逗弄得小鸡巴硬多高,从棉裤裆那里顶起来,自己便不好意思了,想遮掩,我们早发现了,立时一齐声地把他摁倒在雪窝子里,解了他裤腰带,七手八脚地往里塞雪,也立时的,雪窝子叫我们抄塌了,一炉火腾地便熄得冒出一片水汽。
七零年,还是七一年,我在冬天里跟人打雪仗,被人撵得没了跑处,只好往雪坎下跳,大跌一跤,把左手摔脱臼了,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多月才复原。胳膊好利索了,那个冬天也过去了,春天已然草浃浃地铺满大地,从那个冬天开始,我再也没有玩过打雪仗。早年的雪,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,那样地厚实,暄腾,干净。那样的雪,我们是当做棉花睡的,当做白面吃的,它在我们打雪仗时,塞进衣领里,塞进裤裆里,把我们皮肤冰湿,水浃浃地,一会儿发冷,一会儿发热。
我小姑夫人活得极讲究。他一年四季在吃喝上讲究,比如冬天要吃羊汤,羊是自己喂养的,在冬里自己宰杀了,放了热的羊血,剥了羊的皮筒子,成了一个雪白、浅蓝的胴体了。这样的鲜物儿,要用了冬天里见霜去了草气的小水萝卜,再加了各样的草药根根炖了,直炖得热乎,稀烂,入了口不用生嚼的,就直接化入肚子里去了。我老屋里冬日里吃羊汤,兴就了火烧馍泡吃,还要有一大海碗鲜红、碧绿的芫荽辣子,是用了石窝子舂成的,汁汁水水原正,下口直是一股清香。再如夏天里,喜欢用鱼腥草炖汤吃,有鸡汤,有鸭汤,山涧里野鱼儿的汤,有时材料不就手,只加些绿豆也能做成一锅好汤。有一年,受了灾,他就只能用洋芋做汤,也是加了鱼腥草的。那鱼腥草,他直是吃得饿痨,一直吃到老了根了,恰恰吃到冬里了。春天里,人都讲究吃春呀,什么地米菜,香椿,油菜苔儿,刺罗包,罗儿令,灰蝶苋,鹅儿肠,都是大发之物,兴春天吃呀;春茶出来了,最讲究是明前茶的,一定是要喝了一碗明前茶了,才算入了春了。大户人家如此讲究,穷门小户,也要采了野茶,制得一碗两碗的,来个客,喜兴得招呼了人家喝用。小姑夫则与人相反。到了春天,他直是捡旧物儿、陈物儿吃,如煮上年的老脚片子茶喝,吃饭就菜,也直是要吃各类的干湿腌菜,去坡上刨了去年落掉在地里的瘤生子洋芋炒菜吃,好吃,炒不粑,脆生生,用了坛子的酸水炝了,好嚼道。到了春天,我们都上火,就我小姑夫没事儿,他不吃上火的物什儿。秋天日子最好过了,甚样都可放口吃,与人不同的小姑夫,与我们一般地,见甚都吃。也吃新粮食,也吃还没过霜的萝卜白菜,葱蒜辣子。有一样,秋天小姑夫喜欢用猪板油做菜吃,有时,猪板油不就手了,不知他从哪里弄些漆籽油来吃,将就像个猪板油似的,我们都不吃,只他一个人吃得一顿饭浸一嘴圈儿的漆油,像长了一圈的白胡茬儿了。
还有一样,我记得难忘。到了秋里,我小姑夫喜欢到野地里去刨猪獾子、狗獾子,猪獾子长得像猪,狗獾子长得像狗,两种獾子,都是刨庄稼的高手,到了秋里,最害搔的就是獾子了,一只獾子在秋里要养肥了自己,竟要糟害了小一斗的粮食。小姑夫整獾子不用枪,只用烟熏。也不知他是怎生咂摸的,他就知晓獾的洞子在哪搭儿,前洞在哪,后洞在哪,一般地,堵了后洞,只留了前洞的空间,张一个麻网兜子等着,烟从后洞一熏,那獾子必定就从前洞逃窜,昏头窜脑地就落进我小姑夫的麻网兜子里去了。我最喜欢吃獾子肉了。新鲜的獾子肉不好吃,土腥十足,要用灶头的烟气熏上十天半月,才吃。獾肉用坛子里的酸白菜、酸辣子爆炒,最好,下饭,也不腻人,直撑饭量。我小时候在老屋住的三年,年年秋里有獾肉吃。一到秋深了,我小姑夫就要收拾他的麻网兜子,跟我说,我去给咱弄吃货呀!每回必有收获。一个秋天,我每天都可以吃上獾子肉,只要我祖母、大伯娘高兴,而我不会惹得她们致了气了,比如我有时无聊透顶,跑到屋檐沟后头玩火,点燃了草坡了,害得一家大小为扑火糊得戏人似的,她们做饭时,一定要给我炒了獾肉,小姑夫与我一起吃。我至今还喜欢吃獾子肉。可惜不常见着。偶尔回一趟老屋,兴许还能吃上一口。酸白菜,或酸辣子爆炒着,香气和味道甚都有了。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