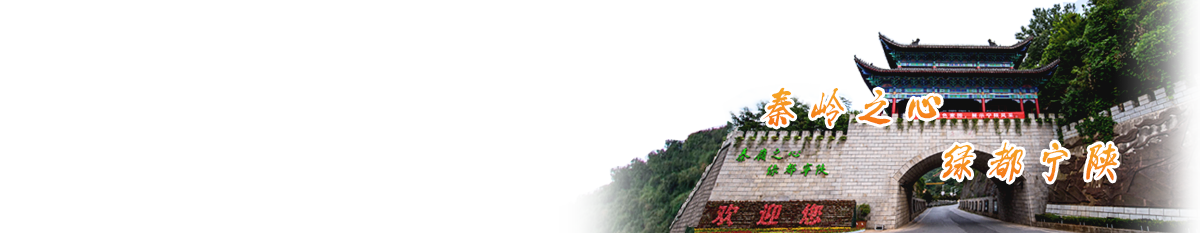文革食谱
我的文化大革命,是从公元1970年以后开始的。从这个年份开始,我知道了什么叫饿肚子。我的文革,就是饿肚子。说实在的,我对文革的恶感不是现在才有的,应当是我刚刚醒事时起罢,七十年代里,我刚能记住个整事儿,就是饿肚子,天天吃不饱,年年吃不饱,胃是个漏斗儿,有点东西装进去,一眨眼的功夫,就漏得没了踪影,因此我的不喜欢文革,真不是马后炮。我小时感性,爱认个死理,比如,大好年月,竟天天吃不饱肚子,我便认为不好,任你说上天去,我还是觉着不好。有些年,说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,是土豆烧熟了,再加牛肉。电灯电话无所谓,煤油灯也能将就,就是没了油,乡下用松树的油节子做成的油亮子,也当灯用过。只是土豆加牛肉诱惑人,记忆中,整个的少年时光,也没吃上一口土豆烧牛肉,至今共产主义的底气便不足。从上小学开始罢,学校里年年都要请了老贫农给我们讲忆苦思甜。一个老长工,大名李家成,小名狗娃子,从他父亲那辈起,就在地主家扛长活,他父亲扛到三十多了,地主发了个善心,把家下一个粗笨的丫环,许给了他做女人。老地主有算计,老长工生下了娃儿,就是小长工,这个讲忆苦思甜的,就是老长工和丫环生下的小长工。到了解放,他已经是做了地主家二十来年的长工了,到了三十岁了,又娶了地主家的丫环,便解放了,小长工和小丫环生下的娃儿,就长在了红旗下,差点又成了小小长工了。我父母在乡下工作时,有年写了他们家的偏厦子屋住,一月一块五毛钱房租。李家成一家一大堆人,加上我们一家人,把个老院子整天吵得热闹。
长工爷爷给我们讲忆苦思甜,起先,讲得满嘴起沫子,一嘴里说的都是旧社会的万恶。说到动情了,我们小小的娃儿们,也动了情,老师就领头喊口号,喊叫打倒地富反坏右,打倒资本主义,打倒帝国主义,打倒刘少奇,还打倒苏修。讲着讲着,嘴上把不住了,大约顺嘴儿发挥着了,说:狗日的地主呀,心狠着哩,七八月红火大太阳的,我们下田薅秧呀,地主家吃肉,半扇子猪肉呀,地主家大小娃儿,小媳妇,婆娘,剔了瘦肉,用青辣子爆炒着吃,蒸肉包子吃,天气大呀,地主家在葡萄架下喝绿豆米汤,吃肉包子,一咬一嘴油唔!我们下了工,吃甚哩?锅里煮着洋芋炖肉砣砣,尽是肥肉呀,锅面子上起一大层油,不冒气,舀一大碗,捧着喝呀,油底下烧着哩嘛,就烫了嘴巴皮么,舌面上也立马起了火泡了么,地主家的就笑话,说个狗日的们,饿痨着哩!长工爷爷说,七八月大热天,给地主薅完秧,吃肥肉砣砣炖洋芋,就锅盔,地主家的,坐在葡萄架下,喝井水镇过的绿豆米汤,就了一泡油的肉包子,一个天下,一下地下,长工爷爷说:狗日的地主,拿咱们长工就不当个人么,搞阶级差别么,我们要打倒他们,不打倒他们,我们就没个好日子过么!
于是我们呼口号。呼得好多同学,口水顺嘴儿流,我也想,旧社会好呀,有肥肉砣砣吃,有锅盔吃,地主也好呀,瘦肉包子、绿豆米汤,可劲儿造,还坐在葡萄架下,一家大小的!这思想要不得,我当然只是在心底里感叹地主生活,感叹旧社会的好饭美食。若是说出口了,那还了得。不过,我知道别的同学,大约与我是一样想法的,你看,一堆子人里,好多都在流口水么!女同学,平时斯斯文文的,这阵儿,也一样不自觉地流口水。我们大约都是对洋芋炖肥肉砣砣心生无限向往了。当然,我也想一想瘦肉包子、绿豆汤啥的,立马又回过思路了,还是肥肉砣砣好哩,实用,解蛔虫,地主那般的吃食,哪是我们无产阶级能胡造的!
就是这个长工,解放后,五八年罢,我听人讲,一次与人打赌,竟造下一个卤猪头、两小升米做熟的糙米饭,把另一个大肚汉比得拉了半月稀,吃坏了。他竟好好的,说是努起屁股放了几个大屁,便球事没得了。这长工爷爷解放后,生下一大堆娃儿,有个女子,还是我小学里的同班同学,人长得可以,就是饭量大。我们三夏时,组织给生产队割麦子,她一顿能吃两个杠子馍,八两面哩,还加一大碗四季豆汤洋芋。吃得做饭的贫下中农大妈直啧啧,叹说,好女娃儿,是个能做的哩,能生养的哩,哪个人家娶了家去,发旺哩么!记忆中,这个长工爷爷也只给我们讲了两三次忆苦思甜,以后就换了人了,不叫他讲了。长工爷爷不讲了,我们十分怀念他,新换的,也是个长工,姓韩,口才不行,还是个结子,大名叫个韩结子,讲了半天,也没有七八月吃肥肉砣砣的情节,尽是旧社会卖儿卖女的事,说自己的大女子苦命呀,说和给地主家做丫环,竟只换了一石包谷,娘老子还想多要一斗白米,地主死活不给,地主就这么占我们贫下中农的便宜么!我们还不打倒地主么!我们呼口号:打倒地富反坏右!打倒万恶的旧社会!旧社会把人变成鬼,新社会把鬼变成人!
这样的忆苦思甜,我们一群半大小子,呼口号没劲头,嘴角也不流口水了。我们只是为长工的口结着急,半天讲不圆转一件事,说大年三十里,长工不敢回家过年,地主家逼债呀,恶毛大雪的,地主狗腿子守在长工家里,不还债就要拿人,拿二丫头呀,二丫头才一十二岁呀。听着听着,我倒怀疑起来,这个长工爷爷讲的是《白毛女》么,是黄世仁么,是杨白劳么,是喜儿么。情节跟电影里演的一般般样。
长工吃肥肉砣砣的事,一直困惑了我多少年。小小的年纪,心生起对旧社会的向往,对地主的向往,对长工的向往,反动罢?!
我父亲是农村出身的,年青时,在外头混了几年,当兵转业又回了家乡,他却是会吃的,见过世面,好些年生变着法,整吃的、整喝的。我们小时候,父母一直在乡下转着圈工作,有时在公社里,有时在大队里,我母亲教书,我父亲收木材,我们有姊妹四个,楼梯坎价大小,正是吃长饭的时候:粮食定量不够呀,我上了初中,才转为三十斤,印象中好多年,妹妹弟弟们都是二十四斤的,我家的粮柜子,有三个隔档,一个装白米,一个装白面,一个装包谷糁,另有一个宝成烟的纸箱子,里面垫了人民日报的旧报纸,专门装一月要吃用的挂面呀。月初,粮柜是满的,到了下半月,粮柜空了。我那时最没出息了,每天要揭了柜盖子,看一看米面,到了下半月,我心下就发慌,眼瞅着米面一天少似一天,算算日子,离下月买粮,还有个多星期哩,有时就想,这差的粮米,怎生凑得上岸呀!
事实上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上有父母亲大人,你个小娃儿,张口货,要你操个甚的心么!
我父亲在公社的木材站里管木材收购,权大着哩:这权力,叫他在生产队里颇有些人脉,每年偷偷摸摸整些杂菜杂豆的,补贴一家大小的口粮,方便得很。每年黄豆下场,我父亲就偷偷从队里买些回来。在各队零星着买,一个队里一升两升,凑拢了,就不老少。不能在一个队里买,太显眼,说大了,是破坏统购统销,说小了,是资产阶级特权,或叫走后门。也有生产队的干部,趁了月黑风高,偷偷往我们家送的,一次十几二十斤。我父亲手里有木材指标,冬月里生产队里搞副业,伐了木头卖给木材站,或把不成器的解成板做成床板卖,做得好的,一个队里一冬的副业,就挣下全年的工分钱了。做这事要有指标,没指标,或指标少了,都不济事。大多有山场的队,都指望着我父亲手里的木材指标哩!我父亲一生清廉,我们工作后,他老提醒我们要规矩,不能乱伸手,伸了手,误人误已,莫得意思。他年老了,更是叨唠得凶相,生怕我们有个闪失,我有时就给他开玩笑,说早在七十年代,你老人家就在腐败么!我们从小就受了影响了哩!父亲笑道:你这娃!那个时候儿是莫得法子么,你们要长身体么,不掏些粮食,饿死你们姊妹几个呀!掏来的黄豆不敢磨成豆腐吃,那太奢侈了,直做豆芽儿:豆芽是菜更是饭哩!
除了黄豆,父亲还到生产队里去掏摸洋芋、四季豆、豆渣、芥菜或萝卜缨子,红红的水萝卜,年成好了,竟能掏些杂粮回来。这些东西都不值钱,但不卖,东西是集体的,烂也要烂在集体锅里,谁伸手,伸手必被捉。这些东西,成了我家那些年,我们姊妹几个长身体的好养料。这些东西,成就了我们家独特的食谱。
黄豆掏摸回来,是用来长豆芽的。我母亲到邻居家,借了米筛,把黄豆的败籽坏粒儿,用筛子浪了去,免得它们长豆芽时,烂根糟须坏事。浪好的黄豆,用个面盆盛了,温水泡一个对时,然后下到我家专制用来长豆芽的黄木桶里,上面用稻草柄子盖了,压上一方青石,再把木桶放置到地炉子的炉坑里,借地炉子的热气催芽,不用三四天,豆芽就长出来了。且慢!长豆芽可没如此简单的,麻烦着哩。木桶里的豆芽,见温就发胀,每天需搬将出来,过清水淘一遍,是谓降温,不淘,没准就焐烂了。豆芽长到约摸半寸长了,不仅要清水淘,还要用米筛簸,是谓簸去豆芽的细根须,没了根,豆芽就直长身子,不簸,豆芽必定长成一团绣毛,细纤纤吃时塞牙,还不增体量,不经吃,因都长了根了,营养也差将了,口味便不讲究。清水淘了、米筛簸了的豆芽,重又放回木桶里,搬将到地炉坑里,只是要加重石头,这叫压根,叫豆芽长粗,长身子,不长根。在我胳膊刚有些囫囵力气后,我家里每天的掏豆芽,就是我每天的功课。一个秋里,一个冬里,再到半个春里,我家豆芽不断天、不断顿,可以说,每一根豆芽都是我看着长大长粗的。那时,一天只能吃两顿饭,伟大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早餐的概念,我家的午饭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,大约有三百六十天是吃面条的。余下那五天,是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