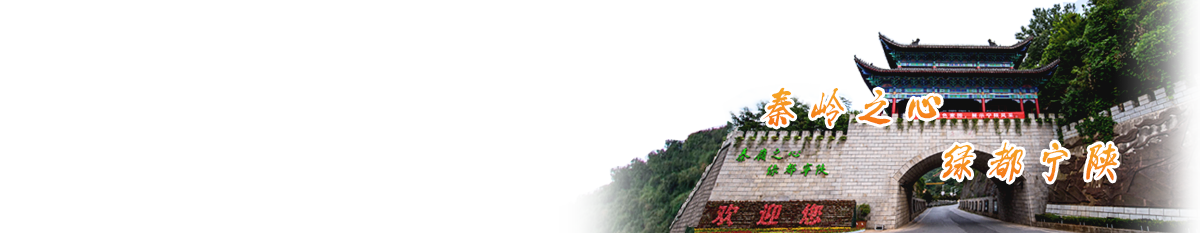静听花开(纪委监察局 邓小鹏)
春日的阳光静静地泻进办公室,桌上的风信子绽出粉红的花,如美人步摇缀在葱绿的茎上,淡淡的幽香里,我走入记忆的花事。
很多年了,一场又一场花事在春天里应运而生,又在春天里溘然长逝,迎春花谢了,桃花渐浓,杏花正酣,槐花儿灿烂出场,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,应着花期碎片样一点点黏上时光的画布。
抑或阳春三月,一大片野花绽放在工地外的泥地,小女孩倚在正修建的楼房窗台,看母亲越过建筑垃圾拔一棵乱石里钻出的青菜,在破砖搭的简易灶上,座上喝水的大号搪瓷缸,丢进细细的挂面,扔进生姜末、大蒜丁、盐、青菜,在汤沸腾时放入葱花、香油、醋,吊人胃口的醋汤面于瞬间产出,小女孩抱着搪瓷缸,连汤带水吸溜,干瘪的小肚皮瞬时饱胀,刚刚还头疼难忍的感冒也在这酣畅淋漓中烟消云散。
大大的天井,春意盎然的梨树,花儿璀璨,小朋友们乖乖地坐在树下,背着手跟着年轻漂亮的阿姨诵读: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……小女孩的手怯怯地伸向父母,要4角钱去街道的幼儿园读书,而父母避而不答的拒绝,姐姐们躲闪的目光,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隔壁的二丫,神气地挎着花布兜消失在院门。
窗外高台上的樱花正浓,几只鸟儿唱着歌飞来飞去地啄食,小女孩愣愣地站在木板阁楼教室的角落,想象自己也是一只自由的小鸟,不再受老师的责罚,而此前只因和同桌上课时小声争论,桃树下那块浸了泥水,埋了花瓣,踩上去东摇西晃,充满弹性绵软的泥地,到底是不是沼泽地。
槐香四溢的时节,蜜蜂嗡嗡,蝴蝶起舞,小女孩搭一张高凳在槐树下读书、写作业,一阵风吹过,槐花瓣儿雨一样洒落,淡淡的清香里,她捧着花瓣闭目凝神,想象自己还未完成的水墨晕染的《春天来了》,一个月后,小女孩在一片唏嘘的诧异声中,骄傲地昂着头,接受校长颁发的美术奖状、水彩笔奖品……
高高的县城转播台,残冬的气息依稀可辨,枯草里一小株紫色的野花正随风摇摆,女孩鹏支着画架,专注地描绘小城的山野之春,近旁假小子扮相的春,女侠样挥舞着树枝宝剑,哼唱着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。没有谁会想到,十几年后,春花烂漫的五月,性格泼辣的春悄然服毒离去,那一场花事正茂,青山之中,当年攀爬嬉戏的痕迹似乎还在,可那花一样的面容却以冰冷的墓碑、黄土的坟茔呈现在一片春花中。
雨下着,教师宿舍里,一张报纸上摊满了月白的槐花,女孩蔚认真地挑选淘洗着花瓣,匀净地洒在电饭锅的米饭上,饭焖熟了,她高兴地推醒酣睡的女孩鹏,喊着:“快来品尝你的劳动果实!”。很多年后的槐花雨,从乡下回家的镇长蔚乘坐的小轿车不幸落入水库,于是,幼小的男孩失去了母亲的庇护,年迈的母亲没了依靠的女儿,纷纷坠落的花雨里,鲜活的花容永远定格,从此校园里十余个少女簇拥假山喷泉的灿烂笑容成为永恒的花事。
春花斑斓的县委机关大院,火红火红的石榴花下,一帮青春的姑娘小伙清扫着大院里的落花残枝,花坛里挖一深坑,埋入落红的花瓣,石榴花一年年绽放又零落,院子里一年一年有人离开又有人走进,姑娘小伙们转瞬升任准妈准爸,夕阳里领着小不点捡拾花瓣,仰望花树一年一年,花依旧,人却不再青春,小不点长了,每一季落红都是新的开始,而春再来时,熟悉的大院,熟悉的落红,已然成为生命里曾经路过的风景。
春夜,母亲家的院场。抬眼,杏花巍然挺立着,一树灿烂,一树星辉,艺术的韵味让人撼然。站在树下,记忆深处的快乐与忧伤,就像散布在夜空里的星星,闪烁着映入眼眸。
春天的雨,淅淅沥沥湿了杏花,湿了心情。父亲多年前搭的葡萄架,朽木新苔缠缠绕绕,和一地的花瓣形成鲜明对比,层层叠叠毫无规律的排列组合,仿佛一幅崭新的艺术画,让人已然觉得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陌生。
杏花树下,父亲抱着呀呀学语的小儿站在树下,小儿胖乎乎的小手塞在嘴巴,口水顺着红扑扑的小脸而下,纷纷扬扬的花瓣落到嫩嫩的脸上,小儿仰头格格地笑……不经意间十年一晃而过,花树依旧,当年的小人儿已是校园里规矩的红领巾了,那个穿着棕色夹克衫,戴着灰色鸭舌帽的老人却静默在黑沙镜框里,不知天堂里的他能否如期赶赴一场花事,聆听落花之中红领巾激情澎湃的演讲。
母亲家的院场,满树的花因为雨的洗礼凋敝了不少,院子里的花瓣被风吹得七零八落,空荡荡的狗舍进驻了一尺多长的黑色小狼狗,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叫声,小小的它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条服役多年的大狼狗,他最后栖身的土地就是那片阳光弥漫、野花铺笈,山野拥抱的山冈,春天里,那个世界的它没准正随父亲共同徜徉于春阳里。
春天里,静静聆听每一场花事。风扬起葡萄架上的几片花瓣,扬花的瞬间我恍惚听到了声声祝福与叹息,就像徐志摩的《沙扬娜拉》: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,道一声珍重,道一声珍重,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-- 沙扬娜拉!”
是啊!纵然春花会适时凋谢,纵然时光会悄然而逝,那些回忆与情谊却永远长存,因为那些一点一滴的回忆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尊重与祭奠,那些记忆背后里的酸甜苦辣就是生命中弥足珍贵的财富,花开花落,韶华难留,我们唯有过好当下,唯有彼此珍重!
- 上一篇:静享书香(双创办 姜方平)[ 04-27 ]
- 下一篇:春天,您好(纪委监察局 邓小鹏)[ 04-27 ]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