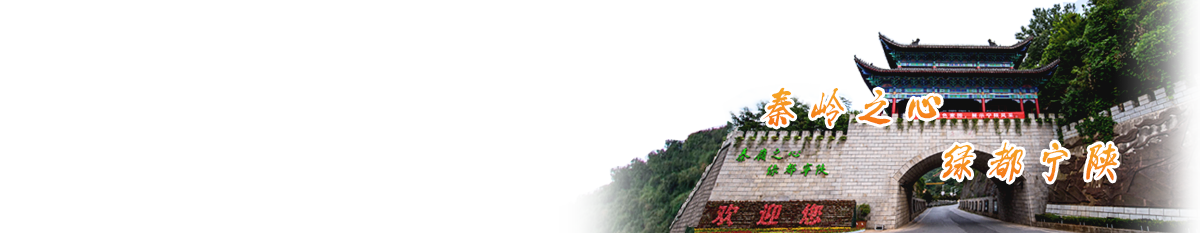老屋三十年
村里的老房子大都被拆了,取而代之是混凝土的楼房。望着轰然倒下的老屋,父亲怅然不已,显然是有些舍不得。父亲感叹道,现在的年轻人对房子没啥感情,好端端的房子,说拆就拆,显得太薄情寡义了。
十年前我从老屋里搬到新盖的平房,与老屋成了邻居,从包含关系变成并列关系,每天早出晚归,我们相互帮衬照顾,两看相不厌。一年前,带着孩子搬离老院子,彻底离开老屋的那一天,喜忧参半,喜得是即将开启新的生活,忧得是很多事情要扛上肩头,内心开始五味杂陈的翻腾,却又不知向谁诉说,更不知从何说起。老屋和我的感情就像是连着胎儿的脐带,不管是离开还是归来,割不断得是藕断丝连的回忆。

三十几年前,父亲凭借一己之力,挖屋场,筑墙板,伐木拉锯,购置青瓦,打造门窗,盖好了三间半黄泥筑成的土房。父亲将自己所有的智慧和汗水镶嵌到土木之中,挥洒了无数的心血和青春,土房是父亲一砖一瓦奋斗的成果,也是他最辉煌的成就和见证。
土屋夹杂着淡淡的泥腥味,看起来低矮陈旧,却透着温馨,除了遮风挡雨,伴我们度过山花一样烂漫的童年光阴。瓦片如同鱼鳞,鳞次栉比的排列开来,夏盛的天空烈日炎炎,院子里热浪滚滚,屋里投下一片阴凉,外界阳光从瓦片间投射一两个闪亮的光斑,我们争着用手接,用脚去踩,在那个缺少玩具的年代,连老屋透漏的光斑都是一种莫大的乐趣。遇到暴雨骤降,瓦片间投射光斑的地方,开始滴答滴答落下雨点或是透亮的雨柱子,我们拿来脸盆接水,有点“床头屋漏无干处,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味道。我们却乐在其中雨点敲打着搪瓷盆,节奏分明,清音悦耳。只有父亲感叹道,房上的瓦要捡拾了(重新整理),我们却不理解他的愁苦。

每到寒冬腊月,房梁下悬挂一块块熏黑油亮的腊肉,一串串红艳似火的干辣椒,我们知道快过年了,老屋里洋溢着着憧憬和欢乐。寒冷驱使着老鼠趁着夜色开溜进屋里,在墙上打洞安家,等到夜深人静,老鼠出来寻找吃的,在木板楼上跑过,如同士兵操练一般。忍无可忍,却又不起床驱赶,我们学几声猫叫,老鼠惊悚不已,活动声响戛然而止。后来老鼠似乎已经看穿了我们的伎俩,任其猫叫声四起,照样活动如常。母亲常说,土墙保温,所以老鼠才在墙里打洞。也难怪即使数九严冬,我家的水缸里也不结冰。我猜熟睡的时候,老屋是醒的,执着的守夜,像谦谦君子,始终保持安静、克制、优雅和简约,骨子里渗透着一种本色的朴素和适度的清贫,与主人荣辱与共,肝胆相照。

老屋见证了一家人的生活,也藏着光阴和故事。每个星期天的下午,母亲房檐下的藤条椅子上折叠衣服,衣服的皱褶经纬里散发着阳光的味道,藏着母性的手温和柔情,还有思念和寄托。我们兄弟三人像盛夏的野草一样疯长,墙上多了一张张奖状,墙角堆起越穿越小的衣服,母亲的缝纫机台面被抓了壮丁---充当临时书桌。
昔日的顽憨少年,转眼陆续离家奔忙。后来我到乡镇教书,二弟外出求学,三弟出门谋生,老屋忽然冷清下来,母亲经常在院子里期盼着我们归来,哪怕是短暂相聚,她都要放下手中活计,做一点好吃的。直到近几年我们都陆续成家,家里多出几个孩子,每到过年过节,老屋又热闹起来。坐在老屋的檐下,听父母聊起陈年旧事,感觉时光慢了下来,心境定了下来,对生活的思索由繁变简。只是父母却已华发盈额,老屋墙壁上的裂缝像一根根暴起的青筋,越来越宽,越拉越长了。老屋蜷缩在那里,有点寒酸不伦不类,有点惨不忍睹。几次劝父亲搬出老屋,他总说土房住着舒服,搬了睡不着觉。每次坐在房檐下休憩,看着墙壁上布满的裂缝,每一道裂缝中封存的风雨、霜雪、悲喜都像赶集似的划过脑海。

毫不避讳的说土屋的三十年是家里最艰难的时期,父亲为了我们兄弟三人上学,一家人的生活,每天早出晚归,奔走在各类工地——河滩的石坎上,新建大厦中,叮当作响砸石场,像是疲惫的纤夫拽着家——这艘小船逆流而上。母亲每天像不停旋转地时钟按时按点,做饭洗衣、喂猪养鸡,操持家务,缝缝补补,一坐下来就会睡着,后来我才明白这都是太累了。

春节回家,村里已经找不到几间土胚房了。看着那些的老墙老瓦,青苔老厚,有点惨不忍睹。我想它们是建筑的符号,是历史的记忆,更是人文的情怀。坐在老屋门口,回忆着不着边际的往事,似是前尘旧事,又像昨日黄花。面对熟悉又陌生的一切,想起兄弟三人在院子嬉戏追逐、母亲又牵又抱带我们逛街的情景,不仅潸然泪下。
我常想一座房屋住久了,就有了你的味道,你的神貌,彼此知根知底,相合相融,记录你的喜怒哀乐,融入生活的一部分。回想和老屋相处的时光,那些记忆汇入生命的河流中,像是波光倒影,悠长而宁静……
- 上一篇:秦岭笔会 2020年第4期(总第112期)[ 05-07 ]
- 下一篇:宁陕观音山摩崖石[ 05-22 ]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