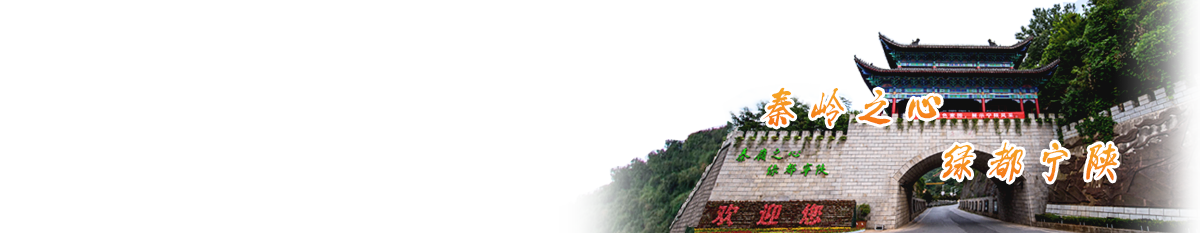消失的乡音
半大的孩子开口就是流利的普通话,让人不得不为现代教育深入人心而倍感喜悦,转念一想,有一天都说了普通话,是不是连家乡的口音都丢了呢?其实多少有点杞人忧天,我常想有一天,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,连乡音都没有了,还追忆什么。有人说这个时代行进的太快了,需要等一等我们滞后的灵魂。

如果说一个地方的食物,塑造了一个人面庞。那么一个地方的山水和环境,培育独特的口音。家乡山多平地少,数百年前,人烟稀少,外地人迁徙与此。口音大抵分为三种,大部分夹杂四川口音,另一类是靠近镇安,口音中透露着关中腔调,鼻音略重;还有一类临近汉阴,却带有江南韵味,俗称江南壳子(客居他乡),猜想大都是江南迁徙于此,经历几个世纪的演变,融入山区,却又乡音不改。
蓦然回首,我们丢失的不止家乡的口音。每次回家,村里的路比以前更平更宽了,但也比以前更很沉寂,养猪的人家少了,养牛羊的人家更少了,甚至连看门的狗也不养。除了公路上呼啸而过的摩托车、小汽车声,村里少了很多东西和声音。这些年,村里的年轻人像一只只迁徙的鸟雀,把事业爱情、喜怒哀乐,一起留在外边,像是断了线的风筝,从村庄飞了出去。
每当走在熟悉的田坎上,曾经朝夕相伴的小河边、水井沿,记忆之门便徐徐打开,透岁月的尘埃,看到了时间从那些黑发渐白中回溯流动的秘密,故乡的声音和往事,又一次顽强执着占领了脑海,思绪穿云端,往事皆茫茫。
每当布谷鸟开始催促春耕的时候,父亲牵着黄牛下地,黄泥随着犁铧翻滚,像是船头飞溅的浪花一样。老牛步履艰难的迈开四腿,脖子上的铜铃在一步一晃之间发出清脆的叮当声,我们紧随其后捡拾地里的草根、石块,有说有笑,父亲吆喝黄牛的声音亲切自然,充满怜悯和慈爱,没有一丝蛮横。每个周末的下午,母亲总要我们打一背篓猪草,大家钻进花香浓郁的油菜丛中,扯一种叫做“窝儿肠”野草,满地野草像是无边无际的绿地毯,我们迅速装满背篓,躺在油菜地丛中,蜜蜂嗡嗡的在头顶闹着,几只蝴蝶迎着阳光翩翩飞舞,无声又忘情,天空中偶尔传来飞机的轰鸣,那时候春天的所有声音都是美妙的天籁。

我家紧邻一条小河,河对岸是一片梯田,清明过后,田里插上了秧苗,有几户人家栽种莲藕。新月初上,点点星光之下,此起彼伏的蛙鸣声,似拉开了初夏夜的交响乐演奏序幕。几个胆大的孩子带着我们兄弟,或是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,等待出来觅食的螃蟹,或是蹲在田坎边,钓黄鳝。母亲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唤我们回家,夏夜里母亲的声音最为清晰,呼唤出浓浓的担忧和爱。
每年中秋将近,梯田里的稻谷黄了,金黄的稻浪随着微风层层推向远方,锋利的镰刀和稻草正进行着一场搏杀与反搏杀的较量,在嚓嚓战斗声中,稻草连片倒下,迎接丰收的洗礼。梯田里几户人家在收割谷子,嘭嘭的打谷声两重一轻,节奏分明,在田野间交相呼应,像一场竞赛,听得人热血沸腾,喜笑颜开,踏实满足。记忆中梯田里的劳作声,是那么淳朴,那么厚重。
北风肆无忌惮的扫过村子,收割完最后一茬庄稼,各种铁制农具已经磨的嘴歪牙豁,有些已经残缺不全了。村头的胡铁匠到了最忙碌的时候,早饭刚过,他扑哧扑哧拉动风箱,火苗乘着风在空中载歌载舞,倾吐出蓝色的言语。乡邻扛着手头的农具三三两两聚到他的火炉边,有的添几块煤,有的开始发烟,聊今年的收成,说明年的打算,扯天南海北的新鲜事。聚拢来的还有我们一群毛孩子,眼睛直勾勾盯着火炉边烤得黄橙橙的洋芋,大人们为了支开我们,分几个烤喷香的洋芋,我们欢天喜地的跑开了。伴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,一件件农具起死回生,脱胎换骨,重新展露锋芒。也许是敲打金属这种强强相遇碰撞,最能振奋精神,至今让人无法忘却。

如今村里梯田都变成了旱地,旋耕机代替了老牛,蛙鸣声早已远去,收稻谷也变成半机械了,镰刀、钢钎、犁耙…这些曾经为居住在山里的人立下汗马功劳,而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,竟然沦落至只能自生自灭的地步。
那些熟悉的乡音,像是村庄上空刮过的一阵风,来过,喧嚣过,却未留下一丝影踪。老人们像牛羊反刍一样咀嚼往追忆远去的往事,还有若隐若现的乡音,诉说一种无法言说的隐痛…
- 上一篇:孝老爱亲的名义[ 08-27 ]
- 下一篇:秦岭笔会 2020年第9期(总第117期)[ 09-18 ]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