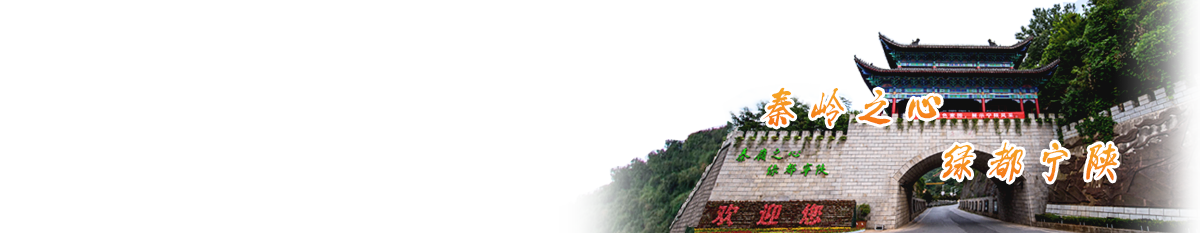忆过年
小时候呀,年关将近,那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种别样的忙碌与期待。整个腊月呀,妈妈就像陀螺一样围着灶台转。她用那古朴而厚重的石磨,一圈又一圈,不紧不慢地推着豆腐,仿佛在演绎着一场岁月的圆舞曲。接着,她又精心炕制血豆腐和豆腐干,那独特的制作工艺,让血豆腐透着别样的醇厚,豆腐干则散发着浓郁的豆香。红豆腐红扑扑的色泽,看着就喜庆。还有那香甜的甜酒呀,经过发酵,浓郁的香气在屋子里肆意弥漫,仿佛给整个家都披上了一层甜蜜的纱幕。到了杀过年猪的时候,家里更是热闹非凡,猪的嚎叫声、人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,奏响了一曲别样的乡村乐章。

终于盼到了除夕那天,我和我哥、我姐就如同奏响过年的华丽乐章一般,满心欢喜地拉开了过年的“三部曲”—— 打扫卫生、贴对联、上山祭祖。当天边还只是泛起了一抹淡淡的鱼肚白的时候,我们家便早早地起了床,一个个精神抖擞,仿佛被即将到来的新年注入了无穷的活力。大家开始打扫卫生,将各处的垃圾聚拢、点燃,再敷上一层薄土。瞬间,烟雾腾空而起,好似被囚禁已久的小精灵迫不及待地要挣脱束缚。我和我哥兴奋地围着浓烟嬉戏玩耍,像欢快的小兔子,蹦来跳去。还时不时地朝着火堆扔鞭炮,响声瞬间打破了山村清晨的寂静,似乎在向邻居们传递着我们迎接新年的喜悦。
接着便是贴春联、门画。我们找来小铁瓢,精心熬制出黏糊糊的浆糊。然后,在我和我哥默契配合下,那红红的春联和色彩斑斓的门画,仿佛瞬间给家门披上了一身喜庆的盛装,让原本略显古朴的家门焕然一新,透着浓浓的年味儿。再在堂屋前挂上两个红彤彤的大灯笼,那灯笼宛如两颗璀璨的红宝石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洒下柔和的光亮,点亮了整个院子,也点亮了我们心中对新年的期盼。一切大功告成后,我们还会像欣赏艺术品一样,左看看、右瞧瞧,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。我妈看到后,总会笑着说:“过年嘛,就得贴上对联,这才有个过年的样子呀。”

约莫下午三四点左右,我爸便会催促我和我哥去上亮了,就是过年了祭祀一下祖坟。打从我记事起,每年过年上亮就成了我和我哥雷打不动的“必修课”。虽说上亮得爬上一段陡峭的山路,但我俩却乐此不疲,仿佛那是一条通往神秘宝藏的道路。一路上,小鸟在枝头欢唱,仿佛也在为新年喝彩。到了祭祀的地方,我和我哥便会收敛玩闹的心性,一脸庄重,怀着满满的虔诚与仪式感,郑重的为祖坟上香点亮。而在上山和下山的途中呀,我们又恢复了孩童的天性,尽情地玩耍起来,或是一颗一颗慢悠悠地放着鞭炮,听那清脆的响声在山间回荡,每一声都像是在山间奏响的欢快音符;或是把鞭炮高高地扔向空中,看着它在空中炸开一朵朵绚丽的“花”;或是朝着树林扔去,惊得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,四处逃窜,吓得松鼠赶忙躲进丛林深处,那毛茸茸的尾巴一闪,就消失在茂密的枝叶间。而我们欢乐的笑声则洒满了整个山间小路,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
上亮回来,家里已经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了。爸爸早已把饭桌、酒杯、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,仿佛在静静等待着一场盛大的宴会。妈妈端上刚炒好的菜肴,那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热气腾腾的雾气升腾起来,模糊了我们的视线,却也让整个屋子都充满了家的味道。接着便开始了庄重的“叫饭”仪式,爸爸神情肃穆,口中念念有词,祈求祖先保佑一家人平安顺遂。我和我哥呢,赶忙点燃鞭炮,那浓浓的硝烟弥漫在院子里,虽说有些呛人,可我和我哥却对这气味情有独钟,还到处去嗅一嗅,仿佛在这硝烟味儿里,藏着最醇厚的年味儿。
待到妈妈把一道道美味佳肴都炒齐了,年夜饭的盛宴也就正式开始啦。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,常常吃不饱、穿不暖的年代里,望着眼前这满满一桌子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美味佳肴,我们三姊妹的眼睛都亮了起来,那眼神中满是惊喜与渴望,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,大快朵颐起来。尤其是每年除夕那一碗干辣椒炒鸡肉,鸡肉被炒得金黄酥脆,每一块鸡肉都裹满了干辣椒的香辣味,那香辣的味道仿佛有魔力一般,渗透到每一丝鸡肉里,光是闻着那香味,就让人垂涎欲滴呀。我们吃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,那满足的模样仿佛此刻吃到了世间最美味的食物。直到现在,过年的时候,这道菜依旧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,只是呀,无论怎么品尝,却再也吃不出小时候那种令人回味无穷的味道了,但它已然成为了我们过年记忆中最珍贵的一部分,承载着浓浓的亲情与对往昔岁月的怀念。
- 上一篇:我和宁陕有个约定(组诗)[ 01-22 ]
- 下一篇:我的父亲[ 02-08 ]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