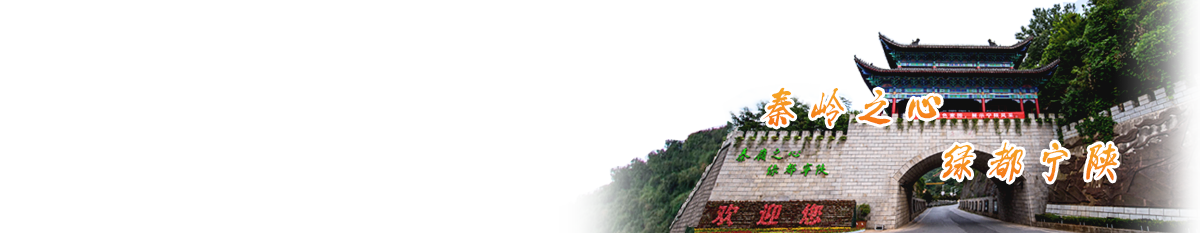饭咕嘟
在我城里的朋友中,正宗城里人其实是不多的。
他们大多出生在乡下,长到少年或青年,读了书,或做了什么发家的生意,进了城了。这些年,朋友们大多很是怀念乡下的生活来。我说,这大约是在城里混得好了,做了人上人了,因之,便有时间、理由、机会或心情去想一想乡下的生活。
朋友们每年总会抽些时间下到我供职的秦岭山里,随便地走一走,随便地看一看,当然,主要的,是能随便地吃一吃。朋友们住在县城的宾馆里,一般情况下,与西安等大城市的一般宾馆也差不多,直是安静,风气上也干净许多,再就是便宜,一般百多元便是数码房间了,山里人实诚,房间的床铺得厚而软和,朋务员也小鸟娇娇时不时地进到房子来,问缺这缺那不。只是小宾馆的饭菜老也改不过劲来,想学着大城市的作派,直是不像,做鱼不像鱼,做虾不像虾,完全没有自己的特色,往往,朋友们住下了,我一般是安排到乡下的农家乐用餐,吃吃土菜土饭。
秦岭里的土饭土菜的确是好吃的。如果不太喝伤了酒,面对一桌乡下菜,一般城里的人还是极易打开胃口的。有个朋友,第一次来,一家三口便吃上瘾了,以后再来,不好麻烦我,自己住到农人家里,换着花样点土饭土菜,很长一段时间,一到周末,自己便开车进山了,一般是周五晚上过来,周日下午返回去,有了两天的乡下的清闲了。
乡下的米面杂豆,是正经自己种着自己吃的。秦岭山里天高地冷,原本不打粮食,早些年城里或乡下吃粮,一多半是靠了外面的供给的。这些年日子好过了,乡下人更是不多种粮了。比如,农民有了退耕还林,国家补着成品粮,一家随便三二千斤的,已然够吃了。直是近些年,有了些改变,农民又开始种粮了,种了自家吃,比如市场上的米是不好吃的,自家便种上一两亩水田,产个二千来斤谷子,自己用打米机脱粒了,留着慢慢吃。乡下自产的米,用了农家肥,也不兴打农药,自然干净得很,加之秦岭里水冷,那稻子白天晒晚上冻,生产期就长了许多,竟然是比山外川道里的米好吃了许多了。比如用了秦岭山里的米煮白米汤,汤面上总会漂了一层米油的,煮得糊了,喝着有青稻子叶的香气。一个人久病了,任甚也不想入口,突然一天就想喝一口白米汤,用了乡下人自产的米煮成了,只喝了一小碗,卧床多日的竟然自己抻着在床上坐了起来,说:再来一碗!农家米养气脉。这是真事,是我一个早年家在乡下的同事形容的。我极相信。比如我公务应酬多了,酒伤了胃口,就会自己煮一碗白米汤喝,一般就有精神。我的宿舍有个小厨房,里面有锅碗,我向乡下朋友要了一小袋土产米,想起来了,就自己煮白米汤喝,养身子,还治病。
乡下的米是糙米,看相质朴,灰灰的,光线好时,仔细地看那米粒儿,有时会看到细细的几乎看不清的米粒上的浅蓝色的毛细的纹路,像极了嫩手背上的毛细血管。有时我看着便感动得很,想那米原来好吃,是因为有着生命力的,是活米不是死米。乡下的包谷也是如此。大手大脚种出的包谷,主要是做猪的饲料的,人吃不得,包谷的珍也好粉也好,囫囵着烧煮了吃也好,都发泡,满嘴地起渣。乡下人自己吃的包谷,是用了心种的,产量并不高,白包谷也好,黄包谷也好,都讲究选择老种子,还是用了家肥,不施农药,那珍呀面呀囫囵着烧煮了吃呀,都粘牙,有香味儿。比如煮包谷珍吃,热的包谷珍盛进冷碗去,用筷子从中间挑着吃,待碗见了底,竟然丝毫不粘碗。这一招,就能看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。城里人往往吃得狼藉。乡下人会吃的不用洗碗。在偏远一些的山里,谷子、包谷、黄豆、洋芋、绿豆、四季豆、扁豆、白菜、辣子、南瓜、茄子、小葱、小蒜,以至于土猪土鸡,依然还保留有老远的土品种,这些年稀罕得不得了。大凡开了农家乐的人家,自家地里种的,一般都是山里掏来的土品种。正宗的土品种,清水煮着都好下得口。
城里的朋友在乡下吃土饭土菜,总是贪相得很。男士倒也罢了,一路来男人的本色便是贪得厉害。女士们也贪,便可爱得紧了。我一上饭桌,便发挥自己做过宣传部长的口才,对桌上饭菜先做一番看似漫不经心的点评,实则是引诱女士们汪出口水来。比如豆腐,我便说山里的黄豆如何土土地长出,如何经了清水的浸泡,如何用石磨磨浆,如何用卤水点得,用细纱布裹得严实,再用青石板压实成型,这才下得锅上得桌,好吃。比如鱼腥草芽儿,要大口地包住吃,可下得燥火,清肠,吃二两鱼腥草芽儿,比得上半月美容。山里的香菇木耳更其地不用说了,怎么解说都是有道理的。秦岭山里有一种大烩菜,里面有鸡、鸭、山药、党参、当归、香菇、绿豆、黄豆、枣泥、鱼腥草、构树耳子,用文火煮得半日,最后成了清芬而浓郁的烩菜,用口面过尺的大号汤碗盛上桌,号称秦岭第一碗,好吃。我的介绍,往往最得女士们喜欢,文相的作派都丢了,大碗大块地吃将得热乎,高兴了,便喝酒,要和男士对喝,喝得半醉越发地可爱起来,天真气叫人刮目相看。有些农家乐备有自家造的土酒,烈性的有包谷酒,里面加了蜂糖,好喝,醉得慢,却不吐,养人胃。有一种谷子酒,用稻谷做的,比纯粹的包谷酒清口,喂热了喝,能治风寒。还有一种文气的米酒。是用糯米做成甜酒,押在坛子里,直咬出老劲来,其色金黄,闻之酒香扑鼻,夏天冷喝,解暑气,冬里加热了喝,开胃口,助消化。山里人叫家酒,城里来的女士大多敢喝。
吃了一肚子的土菜土饭,等于是腾了肚子了。乡下人说得粗,叫起圈。喂猪也好,养牛也好,敞圈常常垫些杂草秸秆,任猪牛拱着焐着,时间长了,便发酵得成熟了,成了好家肥了,需要起了去,备到地里种庄稼菜蔬,把那敞圈腾得清亮,猪牛也清爽。一个朋友听了这般的说法,抠心了半天,再一想,也是,在城里一天吃了五荤六腥,塞了胃口了,猛可地到乡下吃上一顿土饭土菜,还真是在腾肚子起圈哩!
在乡下吃饭,经常能吃到锅巴。早年乡下苦焦,不敢叫饭长了锅巴。有一句土话:除了锅巴没了饭。比如一斤米下锅,不小心长了锅巴,便会有三两米成不了饭。锅巴好吃,却费米面。肚子都填不饱,哪里敢吃锅巴哩。不小心长了锅巴了,饭吃完了,再用米汤水将那锅巴烩了,叫个锅巴汤,一家大小又可喝上一碗了,那肚子没准儿真给哄饱了。这饭食传下来,如今成了乡下农家乐的一道风味。城里的朋友吃了锅巴汤,常常受用得说不成囫囵话,直是嫌自己肚子胀不开。乡下人对此也有说道,说光吃了干的,肚里到底是不实在的,长胃气,打嗝儿,易翻食,喝一碗锅巴汤,等于是给干砌的石坎子灌上浆了,严实,胃气若有,也只能顺肠子往下走哩。
我腾肚子的办法,是每逢周末能回家了,自己亲手做一锅杂烩饭。也不一定非得讲究上好的作料,直是萝卜、白菜、洋芋、剩饭,若是剩米饭,里面再加些面条,整面条要折成小节儿,用猪油烩,开了锅,用文火煨,水一开始就添够,煨时不要翻抄,任它们慢慢成型。这样的一顿,真可以把肚子腾得干净,像洗了船仓般地受用。把这事说给城里的朋友们听,想教他们腾肚子的办法,直是听得多,实践得少,城里人忙,顾不了许多。
乡下的锅巴饭,是用柴火做的,加之是铁锅子,极易做成。那柴火可旺可弱,大火过后,凭了灶里的余火,直把锅底悻出一层可厚可薄的锅巴了。我胃一直不利索,一个中医朋友说,多吃锅巴好。若是下了乡了,我总会注意吃锅巴的。有时主人做饭,若是米还没下锅,我总要央求一声,用柴锅子做嘛,悻些锅巴吃。在城里就不容易了。时间长了,我自己摸索出一套悻锅巴的法子来。我专门买了平底锅,又置了电炉子,将米下到锅里,水添得比米高出两指,打开电炉子煮。先要大火烧开,让米咕嘟一阵儿。平底锅最好是玻璃钢的盖儿,可以直接看到米在锅里的变化。同时要有点耐心,注意观察:你看,米在开水里变化了,水在起沫子,一层层地增加,沫子向四周漫延,密集的气泡在裂变,破了,又聚起了。气泡从锅底生成,在渐渐膨胀起来的米的表面,拱出一个空洞,两个空洞,三个空洞,最中间的那个空洞较大,因此气泡冲起得最高,看着看着,感觉很想是一场火山喷发,在米膨胀起的山头上、坡面上,形成了火山口,气泡的岩浆冲上半空,直冲到玻璃钢的盖子内里,凝结成一层气泡,很快又幻化成一层水珠,顺着盖子的弧面,流进锅里,然后再次升腾起新一轮气泡。在米的表面,明显水气渐少时,那些先前拱出的火山口不觉中叫米饭填满了,表面平静下来的米饭,看不到一点曾经爆发过的痕迹,一切归于平和,这时,可把电炉的火调小,用小火慢慢煨,把锅的四面都煨到,直到锅里水气真干爽了,渐渐地锅巴的香味出来,如果想吃厚锅巴,就多煨一会儿,想吃薄锅巴,就少煨一会儿。方法挺简单。只是真要有点耐心,如果有心,真可以放下大事,做点俗常的家务,了了自个儿的口欲,蛮好。
观察生米做成熟饭的过程,实际上挺有趣。我们平常只习惯端起碗就吃,没多想碗里的米饭是如此壮怀激烈地曾有过惊天动地的蜕变的。那香喷喷的锅巴,做起来也不太难,只要我们能够安静一会儿,耐心一会儿,就成了。这样的法子我同样讲给城里的朋友听,他们往往睁大眼睛,表示很吃惊,很怀疑我描述的那些细节的真实性。
饭咕嘟。这个词很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