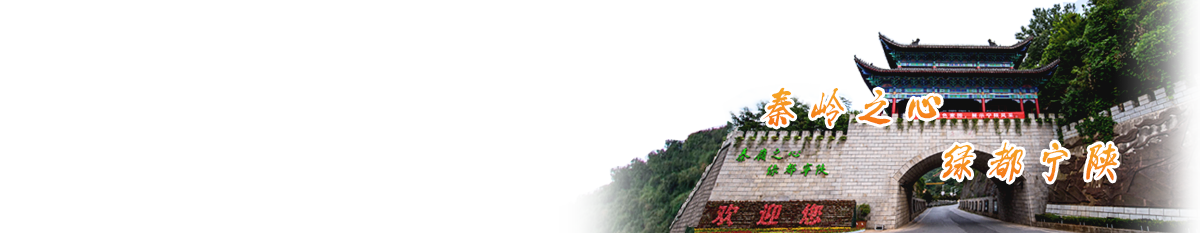最疼我的庄稼
我这多半生,是叫人疼着过来的。亲人们疼我,有时是一碗糠水,有时是一根棘刺。乡下的人,用爱的背面疼人。他恨着你了,就是疼,他爱着你了,却用了刺扎你。这疼,真叫你疼着一辈子的,多少年后,许多的事物都不愿记得,直是乡下的疼人,还在不经意时想起,或在你最不得意时,穿越你空荡的灵魂,像春夏时节的庄稼,爬满地头。
祖父背着沉沉的柴捆子,或掮了大袋的粮食,或扛着沾满新鲜泥巴的犁铧、锄头,走在通向我们老家屋场的那面阳坡上,他向上走,两条腿沉沉的、有力地来回交换,匀匀地出着粗气,坡一点点下降,他一点点上升,时间也在下沉,像涧里的水头下沉,一天价晚地下沉,没有丝毫的响声。常常地,我一定走在祖父的后头,开始能够跟上,渐渐地我落在远远的坡路上了。大林子沉沉,我一点点向上升,树林子和天空依然在我头上升,我老是在林子深处,坡头长长地在林子深透的不知处,每次走,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了坡顶,一出林子,一抬头,看到我家的老屋场了。我总是疑惑祖父为甚总自顾自地走,并不怜惜我的走路的无助。
六七岁罢,那时,我希望祖父能够照顾到我,他能够停下脚步来,撂下背上的物什,歇一口气,等我远远地爬上坡来,挪到他跟前,也能歇上一口气。祖父从不停下脚步,他直是沉沉地走着,上升着,永是在我眼前能见着的地头,走,不停下一步,直到走出林子,看到我的老屋的屋场坝子了。祖父不背负东西时,空着手,也是如此地走着,只要我有胆量跟着他的脚,他在前头走,下坡或上坡,在我眼光能够得着的地头,从不回身望一望我,他似乎并不知晓他的身后,是走着我这么个才六七岁大小的小跟脚的,而我是他亲亲的孙子,他直是顾自走他的。
老家似乎所有的路,无论通向哪里,都是掩在深林里的。路边上的,不是高岩,便是深涧,或者荒草棵子,或是乱坟堆。有太阳时,天阴着脸时,或下了小雨小雪时,或在半浅的夜色里,只要我敢于跟着祖父的脚步,我总是落在他老人家身后远远的地头,我看着祖父一直向前的背影,夜鸟及走兽尖锐的叫声时时响起,四周的神秘气息在逼迫着我小小的胆量,不敢停下来喘气。渐渐的,一个人走路,不毛,不怕,这便是祖父教给我的。
我才在老屋寄住时候,身子是如此地单细,好像从未吃饱过饭般的。我该长的一切部位,比着同龄的娃儿,都小着一号了。比如我的脚杆细而枯干,我的手臂、手背没有多余的窝窝肉,我的脑壳硕大,却是安在一个细细的像瓜蔓子般的脖顶上,我的眼窝深陷,眼珠明亮而胆怯。我的胸廓平坦,肘条分明,脱下衣衫,我的肩胛骨可怕地突出,只蒙着薄薄着的一层皮似的,像极了乡下人窗棂上蒙着的半透的皮纸。我回到老屋,第一次坐到老屋柴木饭桌前,看着装菜的碗,盛汤的碗,添饭的碗,甚至舀满着红艳艳的豆腐乳的小碟儿,都是那么地硕大,我似乎从未见过如此重大的饭场,从此,我喜欢上了乡下的一个老词:饭场子。我吃着乡下我见到过的有生以来最大的第一碗饭,我第一次感到甚是叫吃饭吃饱了。饭可以吃饱么?在乡下,我人生中最初的那几年,我吃饱了饭了。
到了夏天,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我的吃相多么地饿痨。我吃饭时,脱下衫子,光着截小小的身子,捧着硕大无朋的碗,乡下老瓷碗,青白色,不带一丝花纹的大碗,开始是端在面前的,渐渐地,捧在了眼前,最后干脆一只大碗扣住了整个的脸盘子了。我的胸肚鼓胀,圆圆的,像个大汽球。每一顿饭,我都要吃出一头油汗。冬天时,我则非要吃出一头的蒸汽。夏天的大汗,从我脸面上,流下来,经过脖项,再到胸口,流过肚皮了。我放下碗,一定是连出气的缝隙也没有了,我常常知道,放下碗的唯一理由,是饭已项到喉咙眼儿了。
祖母喜欢看我如此饿痨的吃相。一顿饭,她利用一切机会,我停下动作,稍事喘息的机会,给我的碗里再夹一大筷子菜。她能准确地从我的碗背后,我眼前那硕大的碗的倾斜程度,判断出我碗里饭还有多少,然后,麻溜儿地给我添饭。她在一顿饭的整个时段里,无视别人的存在,直关注我的饭碗。当我吃下两大碗饭,她依然用可怜着的目光,盯视着我,说,再吃些么?我若迟疑,便再加上半碗。祖母喜欢笑眯眯地望着我说,一顿三碗饭,皇上不给换。她只关心我的能吃,我吃饱了,她便高兴。
干饭吃完后,便是喝汤。老家的锅巴米汤,是饭后的余事,用来镇饭的。老家人吃了干饭,一定要用汤镇一镇,好比干砌石坎子,用了灰浆勾缝,使之结实。一锅米饭蒸熟,乡下的柴火,总在饭下头,幸了一大层锅巴,早早控起的米汤水,等着人吃了干饭了,多余的饭刮起,只剩下焦黄的锅巴,灶里加一把火,将锅巴炕得起了清清烟汽,米汤水倾进去了,滋地一大声,锅里顿时腾起一片价的水汽,小火焖得片刻,即成。锅巴米汤,清可见碗底,可数清泡化的锅巴粒儿,小口地吹着气慢慢地喝,一时,便真算是饱了。
有时,我玩得兴起,有了个头疼脑热了,一时竟然只吃下一碗半碗的饭了,有时竟然甚也不想吃了,祖母就大惊失色,一双小脚颠进颠出地,要调剂了饭菜了,守着我喝过一碗了,再喝半碗。最没口味时,祖母打了细细的麦面酸菜拌汤给我喝,里面加了生姜,猪板油。有时是小火煨的稀米汤,晾得不烫嘴了,里面加一勺红糖,或蜂蜜,喝过后,嘴里要苦焦小半天,有时晚间喝,早晨醒来,苦味还在舌面上。我小病过后第一碗饭,往往十分盛大,除了满桌子的菜由着我吃,我的饭碗里,一定要有一块几块腊肉拌子,或卧在碗底的荷包蛋。
在老家的几年,我长成了身子了。都是老家的热饭热菜热汤喂养成的。像圈里的小猪架了,像鸡舍里的小鸡儿,像栏里才半岁口的小牛犊子,或像春里新下得的一窝小狗娃儿,小羊娃儿,不到半年,就长出身坯子了,长出骨头架子了,长得有了大模大样的气势,长得虎气了,走道开始生起风了。
我大伯父只要高了兴,便喜欢叫我坐在他的宽大的肩头上,掮了我去生产队的大保管室里开会玩。一般是春里多些。正月过了,二月过了,雪开始在化水,最早在沟楞坎上抽出苔芽儿的水芹菜,有一星米的模样儿了,生产队里便要经常地开会了。大伯父一班人,坐在保管室正当中的大板柜前,屋子当中的房梁下吊着一盏马灯,有几年是汽灯。人围了一圈,挤成了人疙瘩,人圈中间,是一堆大柴火,正烧得旺相,火光照着人的脸,有的白,有的黑,有的油光,有的草青。在这样春天的夜里,乡下的人围坐着,说庄稼的事,他们要在新的一年,种下包谷去,种下洋芋去,三月太阳不冷浸了,洋芋要冒出红芽子;到了五月,谷雨过了,田里要有青青的水稻;水田的田坎楞上,要种了黄豆,所有的用了田里的稀泥抿过的、搭绊过的田坎,都要顺手种了黄豆。这些村里一年的大事,值得在这样红火的夜里好生商量哩!在哈欠渐渐升起一片了,火光淡下来,一村的男女,都知晓了这个春里自家个该做些甚的活路:重活男人做,轻生活路女人做。男人们要耪地,耙田,清地边子,往地里挑驼家粪;女人们则结了团伙忙着浸种,选洋芋种,筛包谷种,跟在男人后头丢籽种洋芋,或帮了男人在地头烧火粪。在初夏,女人们大多都要到秧母田里给水稻下种。这是个细法活路,稻种在队里两段育秧的温室里催出芽盘,再掮到母田里,一星一芽地移栽到抿得细嫩的秧母床上,好叫它们长出壮苗来。在春种时节,在夏种时节,或冬播时节,女人们统一要跟在男人屁股后头,男人起沟垄,女人下籽种,再后头是老汉老婆婆丢粪呀,掩垄呀。栽水秧时,一个村里都是节日哩:为着赶雨水,一村的水田,都要快快地齐齐地栽下秧去;镜面也似的水田,一片价男女的光脚杆,水声人声一片哗哗响,只三五天,镜面也似的水田,就布满青青的水稻的秧苗了,横竖成行,浑浑的水田里,太阳呀,雨点子呀,初夏里的小风呀,轻易就要作弄出水田里的一派生气,很是夸张妖气。
夏天里,我从大伯父的肩头滑落下地后,一般不会老实地在保管室的大屋子里听大伯父开会:我到来时,那里面已是汗味混着屁味,男人们、老汉们,嘴里叨着旱烟袋,明明灭灭的烟火气,早已把嘴张的辣女人呛出一片骂声了,我听到她在尖声笑骂说,没见过你们是在烧落气纸吗,是在煨火粪吗?我直要到屋外的场子玩,领着一群与我同样的半大小子,钻草垛子,比赛丢石头,在场坎边比赛谁个尿得远、尿得高,或扭成一团摔抱架子,我有时赢了,就锐声大叫;有时输了,很是恼火,就跟人一对一地骂仗,骂人家娘老子,骂人家小姑,骂得老气横秋,有章有法。
玩得累了,有时竟在场上的草垛下睡着了。在星子上升到屋顶高时,我在睡梦中听得大伯父叫我的小名儿,有时叫得烦了,便骂我,说,个鸡巴娃儿,死到哪里去了!他的恶声恶气终于叫我一个猛子睡来,沾一头谷草,不敢拿眼去看我大伯父。然后,我伯父将我甩上他的宽大的肩头,我则坐着他的肩,撑着他的大手,像开飞机,一颠一颠地回家去了。星子在头顶,在树梢上滑动;有月亮的晚上,星子都躲了,只有一派月的清光,水一般泻在天地间,泻在树枝上,泻在村路上,有时泻在路畔子前的一块大石包上,一眼望去,是个大家伙蹲在草丛丛里,月光闪闪,是大家伙的眼哩。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