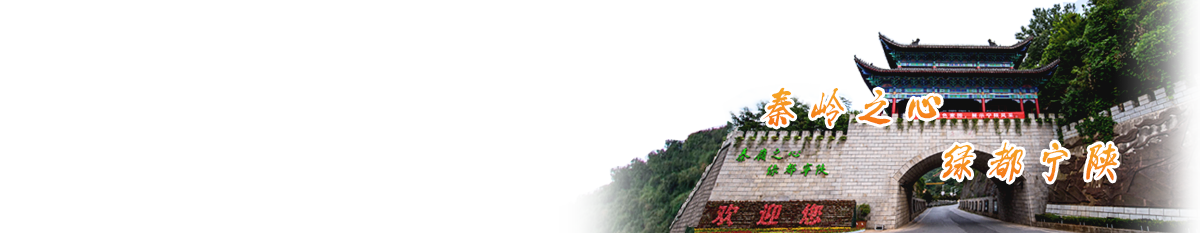山村记忆——爆米花
走入电影院四下飘荡着一股浓郁的爆米花香味儿,夹杂着可乐的香甜,似乎只有此种味道才能与高大上的影院匹配。这熟悉又陌生的味道,仿佛一根引线轻轻一提,儿时欢呼雀跃吃爆米花的情景倏然而至。

本村邻居李大伯,五短身材,古铜色面庞,他是个能人,扎的一手好银针,邻里乡亲,谁崴了脚扭了腰,出不得门,只需带个信给他,他便如约而至,挟着一个棕黑皮夹,慢慢抽出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银针,对准浮肿的部位,稳稳地扎进肉里,我们看得目瞪口呆。如此反复扎几次,不出三天,就可消肿止痛,往往分文不取,称得上针到病除。除了扎银针,我们更开心的是李大伯每年都要为邻里免费炸爆米花,那个年代爆米花几乎是孩子们的主要零食,一个冬天的快乐由他炸出的爆米花开启。
总在寒冬的某一个午后,李大伯带着带着一整套炸爆米花的机器出现在老机房的院坝上,开启了他新一年的炸爆米花之旅。小伙伴们早早地带来了干柴,怀里端着个大筛子,有的装一碗大米,大部分都带着包谷粒。炸米花比包谷花好吃,细腻,没有糠皮贴着喉咙,但是舍得炸米花的人家不多,那个时代稻米产量不高,谁舍得把米这样炸了当零食呢?李大伯开始摆弄设备,一个爆米花机,一个手拉风箱,一条长龙一样的大麻袋。他划根火柴点燃松油亮子,小心翼翼把火苗吹旺,拧开盖子倒进玉米粒,细细的火焰均匀的舔着爆米花机,浑圆的铁家伙像是罗汉的大肚皮,乌黑铮亮。

火燃旺时,也不需要拉风箱,火苗趁着北风在空中载歌载舞,倾吐出蓝色的语言,像是和爆米花机在对话。气压表的指针已经转到头了,爆米花要熟了,我们目不转睛的盯着机器,像是要见证奇迹,又像看变魔术,谁也不愿意错过最精彩的时刻,李大伯吆喝着让大家躲开,将米花机一头塞进口袋里,用撬棍一撬,嘭的一声,像是炮弹出膛,烟花升空,火箭上天般的美妙和璀璨,爆米花倾巢而出,黄橙橙的像是隆冬的雪花,又像初春的花骨朵儿。刚出炉的爆米花又香又脆,大家一把把将爆米花塞进嘴里,肚子胀的像小蜜蜂一样,直到夜幕降临。
有一天黄昏时候,我抱着一筛子的爆米花往家走,忽然想要一个自己的爆米花机,以后想炒多少爆米花,就炒多少,啥时候吃都行。我把想法告诉父亲,他一听,鼻子里哼了一声,买一个?你说得轻巧,你知道需要多少钱吗,到哪去买。我想肯定需要一大笔钱,家里是拿不出这笔钱的,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买。我的梦想,被父亲的一瓢冷水浇灭了。

放学回家,我想到爆米花机不就是一个放在火上的铁壳子吗?于是,找来一个废弃的铁饼干,装进一把包谷粒,盖紧了盖子,放到每天上学提着火盆上,在炭火中烘烤,不时的翻动几次,最后冒着烫手钻心的疼揭开,还真有几粒包谷粒裂开了花,我欣喜不已。第二天,自鸣得意地将火盆、饼干盒、包谷粒带到学校。趁着下课间隙,和几个小伙伴,吹旺了火苗,将包谷粒装进饼干盒里,正在烘烤,铛铛的破钟敲响了,不敢迟到,又不想舍去到嘴边的食物,只得冒险将火盆带进教室。伴着朗朗的读书声,我似乎听到爆米花裂变巨响,一声声叩动着心门。但又不敢溜去取爆米花,不一会儿,爆米花变成股股青烟,升腾弥漫到了教室上空。结果可想而知,连着火盆和心爱的爆米花一起被扔进了校园外的水沟里,还招致一顿数落。我的第一个发明也就此夭折了。
说不清李大伯炒过多少锅爆米花,给村里的孩子带来过多少欢乐,他业早已作古了,记忆力只剩下残存模糊的影像——满手老茧和柴火映红的脸庞。我想故乡的味道不仅雕刻一个人的面庞,还渗透到舌尖味蕾,甚至可以抵达记忆最深处。
- 上一篇:江口回族镇:小镇工匠美名扬[ 09-06 ]
- 下一篇:2019秦岭生命科学探索之旅-国庆亲子特别版[ 09-24 ]
- 国务院部门网站
- 各省政府网站
- 市政府部门
- 兄弟县区
- 县直部门网站
邮编:711699 县政府办公室电话:0915-6822122 邮箱: nsweb@126.com 备案编号:陕ICP备05010792号